子学复兴与晚清文章学“宗子”新风
蔡德龙
《光明日报》( 2024年05月06日 13版)
王国维将有清三百年学术裁为三段:“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文章与学术、文章学与学术思想史的关系向来紧密,王国维“道咸以降之学新”的判断自然也包括文章学在内。晚清既是学术思想趋于多元之时,也是清代文章学的一大转关。文坛出现师法周秦诸子的“宗子”新风,这与彼时子学复兴思潮有密切关联。
先秦诸子与汉魏子书在后世多被视为驳杂之书,在晚清却迅速升温。其在清代地位的升降,可从官方态度的变化窥见。康熙有“诸子百家,泛滥诡奇,有乖经书”的训示,在责令搜访善本图书时,明令诸子书不在收录之列(《清实录》康熙二十五年);直至嘉庆仍认为诸子百家不过是“艺余”而已;而到道光时,时局大变,诸子地位也随之骤升。1838年,道光以《管子》《荀子》为题策试天下贡士,求助诸子以救时局之用意明显;到光绪年间,诸子学课程则已被列入《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成为官方指定课程了。
古文典范的转移
受诸子地位变化的影响,清人的古文师法对象也有转移。清中叶以前,虽也有效法诸子的,但远不及以史为师普遍。桐城派由唐宋八家上溯《左》《史》,重叙事之学。随着诸子地位的提升与子学复兴,以子为师风气大盛。“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不足为”(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士人久病于桐城末流的词意枯淡、气骨薄弱,转而远绍周秦诸子。典型者如“龚定庵、魏默深纵横学《国策》,廉悍学《韩非》,颇足补桐城之所未逮”(朱一新《无邪堂答问》),甚至连《孙子》《吴子》这种纯粹的兵书,也被挖掘出文学性。包世臣从《孙子·兵势》中悟出“繁”与“复”的行文之法。朱凤毛(朱一新之父)则有《孙子吴子》诗云:“行文消息用兵同,古法难拘在变通。我读《孙》《吴》得文诀,临机驱遣寸心中。”将《孙》《吴》兵书等同古文经典看待。
文章选本中诸子文章的增多,以及诸子文选的增多,是“宗子”观念的最直接体现。在经学一元解体、子学思潮复兴背景下,诸子“道”的正当性、“文”的艺术性重新被肯定。刘师培通过考察古文选本发现:“近人所选古文,多以诸子入选。”(《论文杂记》)。从编纂目的而言,这些选本或偏于诸子文章学一面,以期救桐城派气衰语弱的弊病,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吴汝纶《桐城吴先生点勘诸子》;或偏于诸子义理思想一面,期望借助传统子学应对世变。如道光年间吕缉熙编《诸子述醇》,认为“周秦诸子之精说,有宋儒所不及者”。光绪年间李宝洤编《诸子文粹》,以《管子》《商子》《韩非子》等法家及《荀子》《新书》等倡议改革的内容居多。
诸子地位的升降
总体而言,周秦诸子在晚清地位急速上升,但彼此间升降有别,主要还是根据其对时局是否有急救之效而定。林传甲编《中国文学史》时,不按时代次序而是以“有用”与否来排序诸子。他将提倡富国强兵的《荀子》列在诸子之首,其次为兵家经典《孙子》《吴子》,再次为算学名著《九章算术》,从次是被视为与科学相通的《墨子》,最后才是出现时代最早的《老子》,完全以现实价值来定诸子地位。
从现实价值出发,诸子地位在晚清颠覆最大的或许是《孟》《荀》二书。宋元以后,孟子其书其人以位列《四书》和“亚圣”之尊而影响极大。荀子的地位便低得多,甚至被后人视为异端。《孟》《荀》分列经、子,地位悬殊,直接影响到对其文章的评价。吴敏树说《荀子》不仅其道较《孟子》“多疵”,其文也“去《孟子》固远”(《书孟子别钞后》),这是从文与道两个方面扬《孟》抑《荀》。清中叶以来,《荀子》地位得到上升,渐可与《孟子》一较高下。汪中《荀卿子通论》便称“孔荀”不称“孔孟”;特别是在晚清,《荀子》因其重军事、经济更加受人重视,这影响到文章学上《荀子》地位的提升。康有为比较《孟》《荀》二书,提出“荀子文佳于孟子”(《万木草堂口说》)。他说“孟子跳荡,荀子朴实;孟子笔虚,荀子笔实”,从虚实角度评议《孟》《荀》文章高低。《孟子》言性善、言人心而“虚”,《荀子》言礼、言富国强兵而实。喜读《荀子》的包世臣表面会通《孟》《荀》,实则以《荀》代《孟》。他将“性恶说”解释为“激愤之言”。《荀子》说“善者伪也”,伪即是人为,包世臣将其解释为“即《孟子》言‘扩充’之义耳”。《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包世臣认为这同于《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之“道”既被“平反”,就为推崇《荀子》之“文”铺平了道路,包世臣将《荀子》之文直推为“后世文章之鼻祖”,认为《荀子》下开《韩非子》“奇宕”与《吕氏春秋》“平实”两路(《与沈小宛书》),这实质上是在桐城派之外,以诸子建构了新的文统。
文人身份认同的变化
晚清文章宗子,不仅催动古文革新,也带动了文家自我身份认同的变化。文章学上的“宗子”,是在文章创作上主要以周秦诸子及汉魏子书为师,即“以子为文”;而随着子学思潮的复兴,“自成一子”的人生理想成为许多士子的追求。士人从“宗子”到“成子”,身份认同上出现了从“文家”到“子家”的新变化。晚清士人,多不甘于以文人自居,所谓“古之贤者,其志趣殊不愿以文人自命”(曾国藩《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钱穆回忆与其有交往的清末读书人云:“他们的向往,就是做一个‘新的子学家’。那时候孔子儒家已经不是大家共同必尊的,儒家已经衰了……他们要自己来一套思想,要学东汉的王充、仲长统这许多人。”(《经学大要》)在“以子为文”的同时,有意将文集撰写成结构严密、宗旨明确的子书,从而实现“以文/集为子”。早在清中叶,洪亮吉《更生斋诗文集》卷首便有二十篇《意言》,类似《论衡》;其后宗稷辰《躬耻斋文钞》卷一为十八篇论体文,实为一部首尾相合的子书;刘熙载文集《昨非集》卷一收录的《寤崖子》实为一部系统的“宗子”著作;郑献甫自称其集合子、集一体(《著书说》);俞樾《宾萌集》分论篇、说篇、释篇、议篇、杂篇,是借鉴《晏子春秋》之例;凌堃《德舆子》是由《正名》《默化》等九篇文字构成的一部哲学专书,作者则径以“子”命名。
需要指出的是,汉魏以降虽不乏立志成为一子者,但子书已成为较为纯粹的“立言”工具,与多为救世而作、言行统一的先秦诸子书不同。正如日本江户学者服部元乔所说:“余读古诸子书,未尝不喟然叹曰:‘古之立言载道,曷尝不施之行事哉!’”(《猗兰子序》)晚清复兴的则是先秦诸子应世救弊、立言与实践统一的传统。以包世臣为例,他在少年时便敏感地捕捉到“殆将有变”的气息,“于是学兵家”,在读了《荀子·议兵篇》以及孙、吴、司马诸家兵法之后作《两渊》十六篇,时年仅十九岁;后“又见民生日蹙,于是学农家”;又为了“劝邪禁非,于是学法家”(《再与杨季子论文书》);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借子书形式陈述改良主张,被俞樾誉为 “《潜夫论》《昌言》之流亚”(《致宋恕》);龚自珍《明良论》四篇论清廷用人弊端、主张君臣共治;汤鹏《浮邱子》则以十二卷、九十一篇的巨大篇幅讨论军国利病,被姚莹誉为“自成一子”。可见晚清诸子不仅是“高谈阔论”,同样是追求“施之行事”的,是对先秦诸子精神的继承。由单篇文章的“以子为文”演变为文集仿照子书的“以文为子”,是晚清子、文/集合一、泯灭部类边界的新现象。
中国文学向来有文本于经的传统观念,《文心雕龙》更是明确提出“宗经”之说;而自唐宋古文运动以降,古文家学文多以史为师,客观上形成了“宗史”观念;晚清文坛奉周秦诸子为典范的“宗子”新风气,影响及于民国。后经民国文学史著作与国文选本的确认与修正,诸子散文最终得以与“宗史”的历史散文并列,奠定了当下先秦文学史教材中“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二分法的基础。可以说,晚清“宗子”理念对诸子之书由子部最终跨进文学疆域起到了最为直接的推动作用。
(作者:蔡德龙,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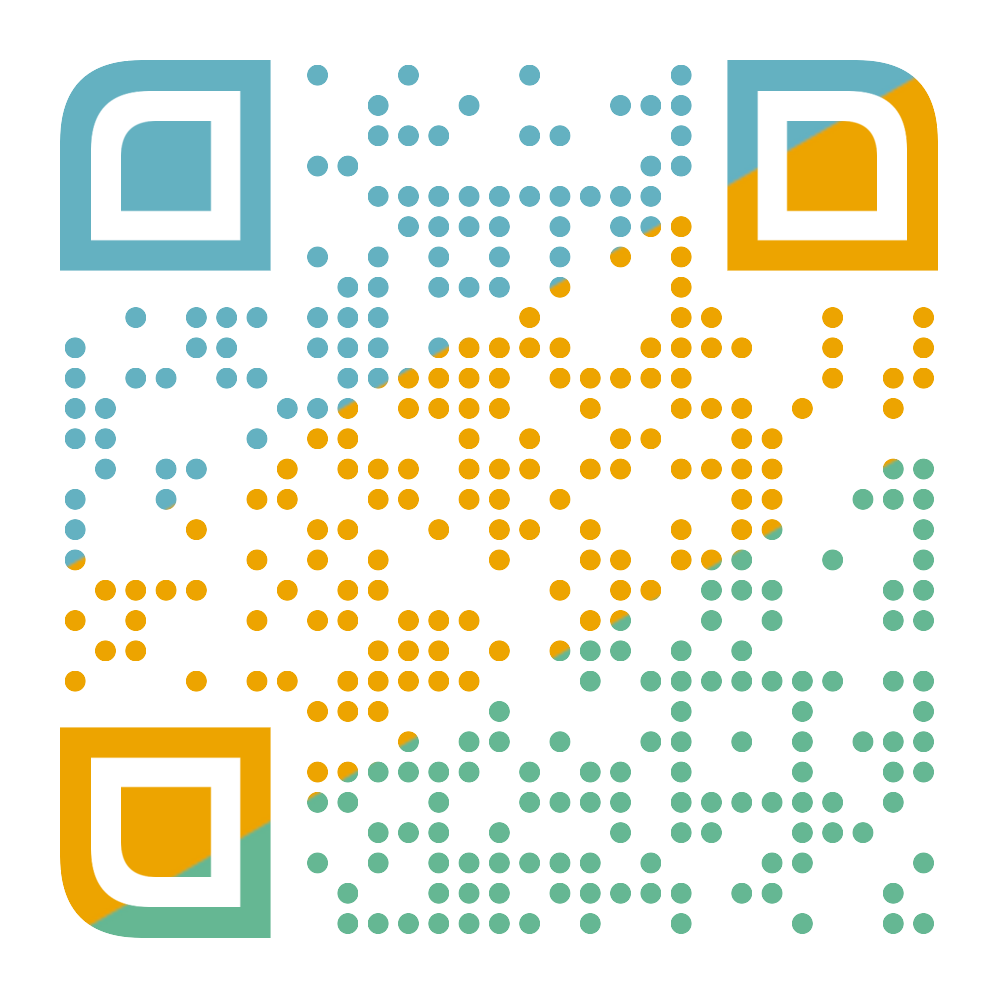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