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无愧的开水白菜‖余庆
无愧的开水白菜
余 庆
恍然一年已过,我经历过双重镂刻的岁月,活在“看人浇白菜,分水及黄花”的诗句中。那些不值一提的清淡之美,被一腔蚀骨柔情浸扰。本来生活的姿态是引颈远眺,却因一盆清水,几片白菜,催生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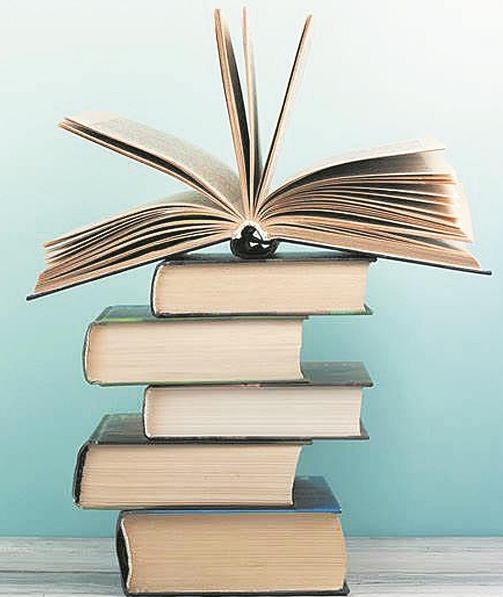
老了,脚步踉跄,一半光阴不负己。嬉戏的心态,妙在人约黄昏后,似乎有了晴耕雨读的浪漫,而心生“诗篇”。
初学写诗,以开水白菜为伴,仿佛“温故而知新”似的,笨拙地爱上这朵花儿。
如此坚持,头脑澄清得像刷洗过似的长出了一百多首诗,孰真孰假,亦好玩而已。在懵懂中思辨,率尔捉笔的韵律和平仄,何尝不依赖绝句和律诗。猜忌五言和七言,又何必“细论人家未尽非”的意义。那些哭哭啼啼“诗兴大发”,宛如开水白菜蘸酱油,久服轻身耐老矣。
缩起肩膀的我,平庸化的基因,是同行评议生命中很重要的印记……虽说入圈很短,人走影随,比别人矮了一截。噗嗤一声,身边颤颤巍巍的诗友,不管是“菜帮”还是“菜心”,大都似大白菜一样,清素寡淡。而我生活在跨界思维中,故伎重演,为赋新词强说愁。
嗟叹,我故作镇静,只需探究天籁声中抵制“价值”的枷锁。是故,想打破风吹叶落去的芥蒂,竟会情寄世故,突然与文学邂逅……假如在相互裹挟中杜撰诗趣,是造物主降临世间,寻求不可多得的文学密钥,还是以观后效的殆尽。
遥想当年,凭什么逃离现世?刻苦不刻苦于我而言,以偏概全的招数,哪有时间去堆叠憧憬!赶巧了,瞎猫遇到死耗子,少了论事之嫌,多了一份吃饱了撑的无聊。这般儿戏,面面相觑,感受“雷声訇訇”都大打折扣了,软软地引发本能反感。
然而,我不是一个懂得照章办事的人,精明一辈子,严重低估了现实的土味。怎么?向来乱劈柴的行为,只为维护绞着、拧着的兴致,怎能不品尝一下开水白菜呢?也是为此,听闻中国式散文诗在国际上是难得一见的“清流”,搁在世界之巅,反倒是孤芳自赏得不到认同。我人畜无害,不屑酬报润,以为诗的韧性能承受酒精的刺激,毋庸置疑地一头扎进诗海,顿觉言之有理。
聆听江湖训示,无暇顾及隔空传味的“嗡嗡”之声,间以我不屑从众,茫然若失地乔装打扮一番,在言谈间绕来绕去,似乎有孤王敞怀的样子,张罗着拿捏自己的命门,故而不幸落入于“某刊”之手,打捞出来的浅薄,是见道之言。
我不是诗人,也不常去充满人间情味的杜甫草堂。虽陪友人晨游此地,大概悟到杜甫的诗笔,反侧自消了。哈哈!殊不稍稍敛住飘逸的仙气,赎得解答,散作大半。我因抄了近道,奔跑在诗歌大道上,确实有点吃不消了!以景相对,到头来才发现,回放游侠杜甫,是一件很无聊的事。若有所失的我,啰唆着不休……瞧,既没有为秋风所破的茅草屋,又忘了虔诚拜谒的角色感。以诗至圣,沿途那些墨迹厚重的书法,被噎得透不过气来。形成景观补壁之作,被石刻工艺折磨到简练之至,不过是微火烧煮的一场过眼繁华。
在夕阳西下的傍晚,我有散步后去喝茶的习惯,不知不觉间,把一天的烦恼带回云翳微荡的世界。糟了糟了,像我这样的歪诗,居然真的有人喜欢,难道这引擎般的风骚,把我送回到牙牙学语的状态?我学识浅薄,确实不懂律绝和古绝,觉得娓娓道出兴味,自然得罪《唐诗三百首》于梦中,不过其事实是如此。
我惊叹了,带动着思绪与文学同床异梦之道,更易思迁的寄托,该总结了……
唉!已知酒后地放纵会招来意外的灵感,把酒言欢,拿腔拿调,正宜最贱的觊觎。我平生隔着清风,尽眼力之所及,线描一变,满目是“丹青”。我自谦,以身示仁。哪怕包裹紧致,层层洇染的大白菜,清而溢远,淡而溢身;再次回味,雅素配澄澈的高汤调味,蕴藏着汤味浓厚的真淳。
我昼寝所思,夜梦写诗,俨然地成了一个“文学发烧友”。从去年秋开始,不知哪来的自信,断断续续便直灌肺腑。某日,有精于诗词的朋友看了“这不是诗,是僵尸的‘尸’,不是诗歌的诗。”而有的诗家看了“这是辛甘厚味的好诗。”看来,批评与表扬对我而言,给人识透,意脉相连。偶尔,我喜欢去倾听电话另一端的述评,不知所终,且置之不答,还真是个“清香爽口”的技术活儿。
其实,给灵魂点一滴朱砂,诗情早已沉浸在一个字、一杯酒之中。我积淀已深,如江水滔滔,横冲直撞。在《一凿一匠》的小舟上挂着自信的风帆,信步游航,将惊奇与恐惧转化成幽默和甜蜜。如上,不惜装腔,保持风格比保持身材重要,颇不容易。亦如黄永玉之言:“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地喜欢,站在太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
我以任性迈入诗界,不管三七二十一,肆意带去问候。也许,写诗是自身的活儿,投稿刊发是社会的事情。况且,我从没进入诗门,只是在堂名匾下待一会儿,有些混沌初开,不自量力也。于是,马不停蹄地“敲门”,闲言碎语依旧有诗,人心的润泽,在前辈眼里那不是诗,是生活于此的始奠……虽没定论,就归于寂灭,心中黯然地起了疑惑与悲哀,却有闲工夫在诗里扯淡。
微皱着眉的我,被某一个画面唤醒,有一种远方比开水白菜更甚!论讲究,无从猜测。嗜吃香醇的开水白菜,因少盐少油,方显本性之大美。这是川菜名厨黄敬临在清宫御膳房时的拿手好戏,虽贵为国宴上的一道精品,但汤味与鸡鸭相似,无非是因为有好味之理。不疾不徐,我鞭辟入里的食经,照样啖着焯水过的菜心,像挂着几朵云霓的妙解,是何等奇妙的菜中极品,竟然不可思议变得柔软熨帖……
久而久之,我明白了情致宛然的句式,伤春惜花,曳杖而行。这般舍取,像我这样的年龄,仗着脸上的胡碴,令人猜不出情绪。鉴照一口白菜,抱膝而吟,才知鲜美的开水白菜,稚嫩而老练。我点火生炉,将母鸡、母鸭、火腿、肘子、干贝、花椒等食材,精心熬制十小时以上所得的高汤,在滚烫中一瓢羹下去……怪不得嘴唇容易黏住,幸福得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不重复别人,万物互为师学,更不重复自己。
是啊!觉得可惊,又觉得可笑。觅我散文和诗句之间切换的熟稔,丢掉了“自我衬托”的幻想,犹恐听到煮沸而琐碎的响声,嫌白菜叶有破损的骚味,有了局促不安之相,估计是惹人烦了。
有道是不解尴尬,相逢是梦中,实在不是以图一己的苟安,是我所愿之事。
来源:《成都日报》2024年3月12日第8版
作者:余 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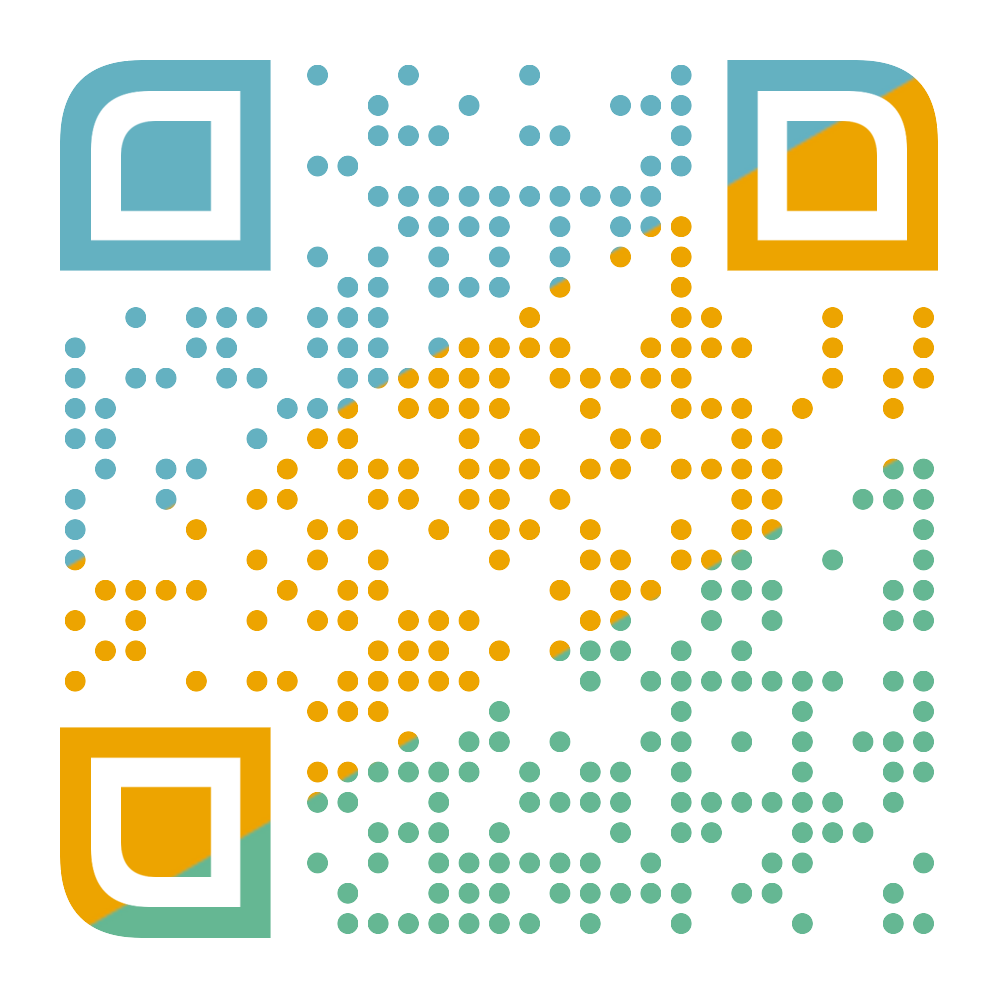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