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向西北的拓展——来自姚河塬的证据
20世纪下半叶关于西周时期的考古学发现曾极大地佐证一些关于周的传统认识,即周是渭河流域关中平原的一个小部族,推翻商王朝后建立了新王朝。为了管理西北和东北延伸至今山西省、河北省,东至山东省,南至淮河及长江中游的广袤的新征服领土,周王室派遣姬姓成员及其盟友至新领地建立诸侯国。
通过这些诸侯国,周王朝能够在四面八方的广袤领土内施行其政治统治。广交政治盟友和建立军事据点被认为是周王朝管理庞大王国的主要策略。许多诸侯国,如晋、燕、鲁和曾,都通过考古发掘得以辨认,它们的政治和文化图景在近几十年内得以考察研究。周王朝势力向广大的西北地区拓展,或许也是新兴王朝的既定目标。近十年的考古发现为这幅图景增添了很多细节,同时也说明在中国青铜时代,北方和西北方地区的政治和文化远比传统文献所记载更加复杂。
姚河塬遗址位于泾河流域上游的六盘山东麓,毗邻周王朝控制的关中地区。传统观点认为,在商晚期,周曾在此区域开展军事斗争以消灭敌对势力。因此,姚河塬遗址对我们理解东亚青铜时代姚河塬的居民与周王朝和其他地区之间关系的性质极其重要。同时,姚河塬西周时期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对揭示东亚青铜时期的文化新景象也有重要价值,使得首次多维度审视区域群体成为可能,为讨论这一地区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重要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
西北地区的一个区域中心
姚河塬遗址所在的宁夏彭阳县新集乡姚河村,位于黄土高原腹地六盘山东麓泾水流域上游支流的三角形台地上。刘家文化(商时期关中平原的考古学文化)的陶器在姚河塬的出现表明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也许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两千纪,但当时的居民是在商的控制下还是自行建立本地政权,目前尚不清晰。遗址中大量的西周时期遗迹证明,周文化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强大。
姚河塬遗址的总面积在96万平方米以上,已经发掘的遗迹包括高等级墓葬区(包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城墙、铸铜作坊、道路、灰坑。考古调查还揭露了沟壕、大型夯筑的建筑基址、道路、水渠、制陶工坊。调查中发现一些蓄水池,有的干渠与水池相连,与铸铜作坊、制陶作坊密切相关。这些证据表明,该遗址的拥有者掌握了较高的水资源利用能力。
一条壕沟和南北走向的墙体将遗址划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面积为56万余平方米,其东部和东北部为高等级的墓葬区,墓葬区的南部为铸铜作坊和制陶作坊区。中部有一个大型夯筑的建筑基址,疑为宫殿区。内城的东南部为小型墓葬区。外城总面积约为40多万平方米,有房址、灰坑、窖穴、窑址、道路等遗址,属于一般的村落及生产、生活遗迹。整个遗址的水系比较发达,水网密布,沟渠纵横,出土了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陶范、玉石器、漆木器和骨角牙蚌器等文物。一些骨器上还刻有甲骨文,目前发现的甲骨文有150余字。
总体来看,姚河塬是中国西北唯一一个有如此丰富多样的考古学材料的遗址,其空间布局现已较为明确,关于聚落、居民活动和手工作坊的证据也已较为明晰,这对探索西周时期大型聚落结构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高等级墓葬区
姚河塬遗址发现有殷商、刘家、寺洼、周人以及当地特征的文化遗物,展现了不同文化或族群的混合现象,其中包括本地人、来自北方的移民及可能被重新安置于此的带有商物质文化特征的群体。商式器物和习俗较为明显,商式簋、矮领瓮、菌首状鼓风嘴均有发现,并且姚河塬墓葬广泛使用腰坑殉狗、殉牲,甚至大型墓葬中有殉人。姚河塬遗址有5种以上的人群混居,表明边疆地区人群的复杂性,也反映了周人与西北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和谐共生的场景,这与文献记载也相吻合。对人骨遗存开展体质人类学、骨病理学、分子考古学与DNA骨化学等多学科手段研究,可揭示各阶段和不同等级人群在聚落内以及墓主人的性别年龄结构、种系构成、来源、群体遗传性状及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食谱结构、营养健康状况等方面特征。
根据C14测年结果,姚河塬遗址东北部高等级墓葬区属于公元前11世纪中期至公元前8世纪中期。大中型墓葬有殉人,整个墓地殉牲普遍,种属有马、黄牛、山羊、绵羊、鸡、犬、兔子等。这种周围墓葬与大型墓葬相连而构成组墓葬的特殊现象是西周考古的首次发现,墓地的中部4组互相连通的墓葬可能属于四代诸侯国君。正在进行的人骨DNA研究可能为这一说法提供证据支持。最大的竖穴土坑墓的墓主人推测为另一位国君,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姚河塬高等级墓葬区至少埋葬了五代诸侯国君。
所发现的马坑和车马坑从北、东、南三个方向绕着墓地的外围呈弧形埋葬,西侧为一段南北向的壕沟。所有墓葬均没有突破马坑、车马坑以及这条沟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由马坑、车马坑和沟所组成的封闭范围。
这些墓葬虽然规模庞大,但是在发掘前已经被破坏,所保留下来的器物很少。考虑到遗址内发现的手工业作坊包括成熟的铸铜体系,因此这些随葬品比如青铜器,很可能都是在当地制造的。但是许多奢侈品如原始瓷、象牙器、天河石、玉器等不可能产自当地,更有可能是通过交易或其他交换形式到达这里。
铸铜作坊和殉葬马匹情况
铸铜作坊区位于内城东北部,经勘探发现的遗迹有水渠、储水池、储泥池、掺和料堆积、烘范窑、房址、灰坑、道路等遗迹。铸铜作坊区内探方地层及灰坑出土较多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罐、簋、豆、盆、盉、瓮、甗等。所获陶范有1000余块,主要分为容器范、兵器范、车马器范、工具范、纹饰范等,多数成型面保存较好。经过实验室分析,陶范存在泥料高、低黏土混用的现象,通过表层和成分对铸造过程进行控制,并且已经达到借助涂层将铸芯从某些铸件中完整取出的工艺水平。宁夏地区已知的铜矿产地只有中卫照壁山一处,开采时间可能从战国开始,与姚河塬有无关系,需要对照壁山遗址进一步开展调查、发掘工作。而大型储水池、储泥池、掺和料坑、炉子、烘范窑、工棚、填埋陶范的废弃坑等,表明姚河塬铸铜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青铜铸造,尤其是复杂礼器的铸造,需要极高的技术能力,西周时期的青铜铸造是一个复杂过程,如果没有对从采矿到最终成品铸造的一系列技术程序的熟练掌握,是无法完成的。中国许多地区都发现了西周时期青铜器,但只有少数遗址发现铸铜的证据。目前发现的绝大部分铸铜遗址都位于周王畿地区附近,在周都邑之外的地区,只有北京的燕国和山西的倗国遗址发现了铸铜的模范。
姚河塬的铸铜作坊是目前所知西周考古在西北地区的首次发现,意义重大。遗址所出土的陶范、泥芯大部分是用来制造兵器、工具和马具,但也有少量的容器范、芯被发现。容器范的出土标志着姚河塬的铸铜作坊除制造工具、兵器以外,兼有青铜容礼器的铸造。姚河塬这一大规模铸铜作坊的发现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学界主流观点,即青铜技术由周王室集中管控。姚河塬大量的铸铜遗存推进了对东亚青铜技术的产业和传播的理解,也为中国青铜时代技术发现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一发现也揭示出,姚河塬不仅是一个政治军事中心,而且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复杂性的青铜制造中心。
再看马匹出土情况。姚河塬墓地马坑可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类,坑内的马匹分两层或三层,上面两层均是经过砍砸、肢解比较破碎的马骨,埋入时凌乱堆放并未做特殊处理。经动物考古学家的判定,这些可能是经人类食用后的骨骼,似乎与丧葬宴有关。与之相反,高等级的马坑和车马坑中,马匹通常排列整齐,骨骼几乎完整无缺并且以一定顺序放置,所葬马匹数量较多,总计120匹左右,单座坑内最多有26匹。尽管在商周贵族墓葬中,殉葬车马的数量通常是墓主人地位的标识,但这一庞大数量的殉牲仍属罕见。据文献记载,六盘山以西的固原地区是一处极为重要的马匹养殖基地。姚河塬大量马骨的出土体现当地饲养马匹的传统,且马匹资源丰富,反映了姚河塬族群的地位和富裕程度。
当地或为周的分封国
在姚河塬被发现之前,没有可信证据能说明周王室也在西北地区建立了分封国。然而,姚河塬的考古学证据首次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姚河塬发现的甲骨文部分刻在骨器上,出土于城址的多个地点,多达150余字,表明文字被频繁使用,内容涉及巡守、战争和农业生产,但最为重要的是记载了“获”与戎人的战争。M13出土的一件甲骨刻辞提到“获侯”,可能是指名为“获”的族群或分封国的统治者。“侯”这一头衔特殊在两方面:其一,这一地区所出土金文表明当地政权通常用“伯”来指称贵族世系中的长者,即氏族或族群的首领;其二,西周时期“侯”是授予周分封国统治者的头衔。
出土的甲骨文同样记载了抓获戎人献俘于获侯的事迹,提供了关于这一地区军事冲突的一手资料,其他甲骨文多次提及“戎人”“戎地”“抓获戎人”。根据这些甲骨文可知,戎人居住于姚河塬以西,频繁对获发动小规模的侵袭。
西周时期,姚河塬之外还有其他族群活跃于泾河流域,余家湾遗址和白草坡遗址就是其中两个。像它们一样,至少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姚河塬可能是周王朝的分封国或盟友,并且维护周王朝在该区域的利益。事实上,周王朝的政治影响一度向西北方向延伸至更远的固原。
尽管姚河塬的族群性质尚不明确,但是此地可能进入了东亚青铜时代的广泛交换网络。比如,当地没有铜来源,所以铜一定是通过交换得到的。又根据初步分析,玉料可能来自新疆和田或甘肃马鬃山地区,天河石可能来自东北地区。象牙制品有梳篦、杯子、笄等器类,部分器物镶嵌绿松石,图案复杂,做工精细,它们的原料应该来自南方。原始瓷器做工精致,有罍、罐、豆等器类,通过考古发现来看,原始瓷有一条由南向北的传播轨迹。这种传播路线所显示的结果,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技术传播,而是实物传播。
总之,姚河塬的发现首次揭示了存在于西北地区的一个强大的地区族群。这些新的考古学材料为展现该族群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大量证据,其从西周早期存续到西周晚期至周人东迁洛邑,贯穿整个西周历史,是具有连续性的周文化在西北地区的桥头堡。这不仅揭示了泾河上游的政治文化复杂性,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周的政治管控和西北地区政治文化复杂性,而且扩展了东亚青铜时代稀缺资源和奢侈品的交换网络。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29日 1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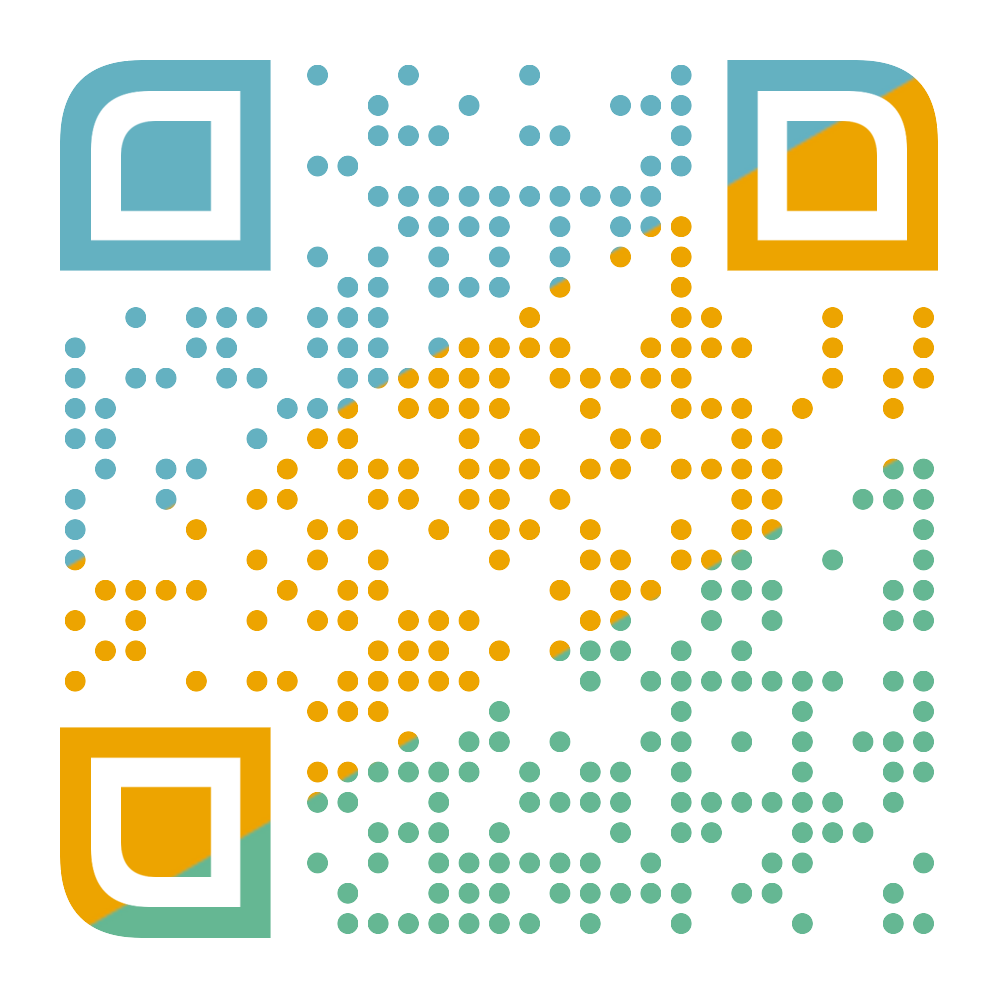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