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老之学领略“实事求是”的精神意蕴
提到“黄老”,我们往往联想到汉初的“无为而治”。其实黄老之学是一门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学问,在不同的时代曾经焕发出不同的精神力量。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曾经这样评论黄老之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黄老之学融合了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各个学派的理论,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正是因为黄老之学总是从现实出发去思考问题,所以“无所不宜”,无论是在战乱频仍的先秦时期,还是天下初定的汉初时期,黄老之学总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为一代代君主提供了平定天下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智慧。
黄老思想发源于战事纷纭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各国的统治者都迫切地渴望统一天下,诸子理论中也不乏对称王天下之术的探讨。在黄老学相关的文献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思潮的痕迹。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一部文献根据唐兰先生等多位前辈学者的多番考证,是战国时期的黄老文献《黄帝四经》。其中《经法·六分》篇有“不知王术,不王天下”,可见《黄帝四经》是有意识地探索统一天下的方法的。例如《经法·六分》中出现了大量对称王之道的探讨,“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地焉,有人焉”,“王天下者有玄德”,“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黄老思想提出了非常进步的政治理念,君主想要称王天下,必须重视天时、地利、人和,而这又要求君主具备高尚的德行,超然于一己得失之外,对有理想、有智慧、有道德的贤才给予极大的尊重。如何尽早地实现天下一统,这是春秋战国的时代命题,面对这个命题,黄老之学提出了非常积极的政治理论。
此外,战国时期黄老思想还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战争和兵学理论的建构。《黄帝四经·经法·君正》篇中有“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由此可知,黄老道家提倡文武并行,德刑并举,将“养生”与“伐死”共同作为国家政治职能的重要体现。纷争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想要称王天下,不仅要懂得治理国家的方法,还要有赢得战争的高级智慧。因而当我们回顾早期的黄老思想,甚至能发现其与兵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黄帝四经》的《十六经》,借助黄帝讨伐蚩尤的故事,传递出一统天下的政治抱负。《十六经·五正》所说的“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直截了当地表示出了对战争的重视与强调。《十六经》还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兵学理论,比如特别重视对战争时机的把握,我们所熟悉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就出自《十六经·兵容》中,就是说如果没有把握好时机取得胜利反而会留下后顾之忧。《十六经》反对主动发起不正义的战争,反对争先、骄纵的“雄节”,坚守处后、谦卑的雌节,《十六经·顺道》中所说的“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因之”,就是以谦卑的姿态等待骄横恣肆者走向穷途末路,而给予其致命一击,这样既可以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也是战争智慧的体现。
当丰盈浩荡的先秦典籍历经了秦火的洗劫,无数文明化为灰烬,汉代初年重生的黄老之学却又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与战国时期有了极大的不同。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汉初崇尚黄老之人甚众:盖公、曹参、陈平、乐巨公、田叔、窦后、王生、直不疑、郑当时、汲黯、杨王孙、邓章、刘德、曹羽、郎中婴齐、黄子、司马谈等都曾学习黄老之术。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汉代黄老之学的特点。《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悼惠王时曹参治齐,曾问道于精通黄老之学的盖公,“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盖公“贵清静而民自定”一言道出了汉初黄老之旨,统治者无为而治,民众休养生息,曹参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齐,齐国因而大治。汉惠帝即位后,曹参继萧何之后成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依然按照萧何注重休养生息的方式治理民众,在历史上留下了“萧规曹随”的佳话。对于此事,太史公评价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太史公一言,道出了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原因。尽管刚刚推翻了秦的暴政,挣扎于水火之中的百姓仍旧奄奄一息。此时天下处于初定的阶段,百姓们内心向往平静安宁,迫切地渴望能够安定地生活,并且极为抗拒严酷的制度与刑罚。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曹参采取清静无为的治国方式,注重因时以养民生,迎合了民众的现实需求,起到了安定民众、稳定社会、恢复生产的作用,为随后到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与强势进取、重视战争的战国黄老之学相比,汉代黄老理论注重休养生息,正是因为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这说明了黄老之学作为一种治世目的极强的学问,是可以适应时代发展而产生变化的,可以“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随着时间、形势、现实的变化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治方略,因而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意蕴。
黄老之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意蕴,为执政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这样评价黄老的,“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在司马谈看来,黄老之术是以道家“虚无”的道论为理论基础,而因顺时势来获得发展的。在这种意义上的“虚无”就是不固执己见、不拘于常法,充分认识到事物发展的情势与形态,以做出最佳的判断与裁决。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内在精神的专一以洞悉万事万物的每时每刻的具体情状,正如司马谈所说:“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如果不能安定精神,那么连准确地认识事物都做不到,何谈提供治理天下的方法呢?因此,黄老之学在道家的精神专一之法的基础上,以体道来获得内在光明,由之延及治身、治国、治天下,兼采百家之长,从而提供与时世相应的治国之术,这种治国之术可以随着时间、事物、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道家理论往往高深浩渺,《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经典治国理论,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遐想的空间。尽管老子已为高明的君主指明了方向,但具体的治国方略,则是由其后的黄老道家所继承并提出的。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庄子这种远离世俗纷扰的道家,其实是被《汉书·艺文志》称为“放者”的,“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可见庄子着力于寻求内在精神的纯粹,试图独以清虚之法处理治国理政之事,虽然绽放出灿烂的理想主义光芒,但是并不能完全切近实用。此时,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黄老道家,秉持道家“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一贯主张,着眼于“道”与现实的结合,弘扬积极入世的现实精神与深切的现实关怀,以期建构可以指导统治者称王天下的理论体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还说稷下先生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人也“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在天下一统的大趋势之下,学者们不再固守门户之见,怀着对建功立业的渴望,热切地寻求称王天下之道,在政治上兼收并蓄的黄老思想因而得以大放异彩,在稷下诸子中流行开来。
通观学黄老之术的稷下诸家,申子主刑名,韩非重法,田子贵均,慎到贵因,邹衍论阴阳,其各有所论,学派归属也是不同的,我们常常因此弄不清黄老之学的真正内涵。其实,司马迁说稷下诸子“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正是说学黄老学的诸子各自有所发明,其各言阴阳、刑名、法术、道德,各有千秋。然而他们的学说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这些思想学说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原因,都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治世之术,这也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所说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在内容上兼收并蓄的黄老思想,其精神实质是指引着学者们发明新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而如果想要提供治理好国家,是一刻也不能脱离现实的,必须随着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们从黄老之学的发展轨迹中,也可以看到黄老思想随着现实状况而不断变化的历史印记,这正是黄老之学在汉代能够重新焕发生机的原因所在。这种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不固守僵化教条的政治理念,可以与时代的思潮紧密结合,体现出了极为高明的政治智慧。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25日 1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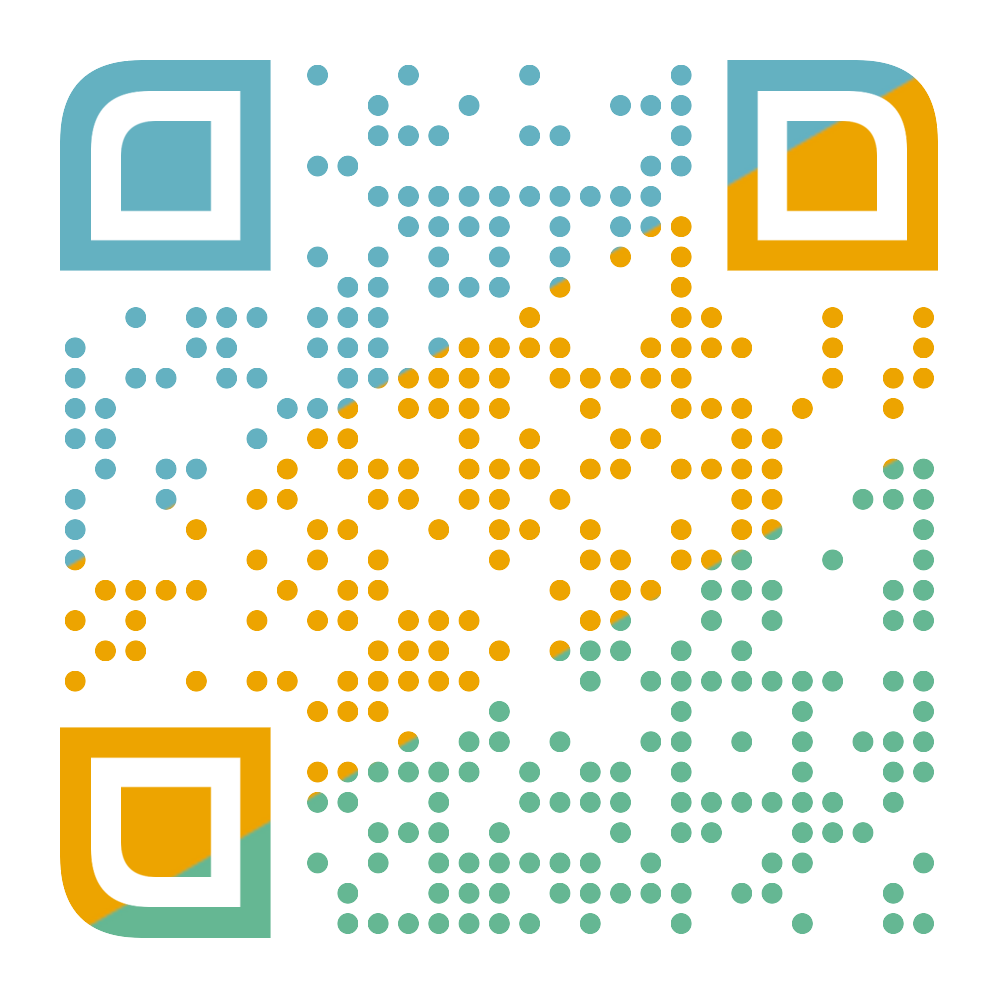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