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式艺术展需要“去伪存真”
谢廷玉
《光明日报》( 2024年05月05日 07版)

1°2°3°4°(沉浸式艺术展)罗伯特·欧文

雨屋(Rain Room)(沉浸式艺术展) 兰登国际
【艺点】
当前,“沉浸式展览”正在艺术文博领域蓬勃兴起。如若基于策展思路和技术运用对其加以界定,则不难发现这些展览多力图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用科技装置和数字媒介令观赏者“沉浸”于作品之中。
“沉浸式艺术”的兴起一般被认为是受到以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影响,这种学说重视人们通过亲历而获得的“感知”多过于普遍有效的“认知”。梅洛-庞蒂曾以“蜜”为喻:只有通过感知能力与“蜜”进行接触、交缠,人们才能体会到独属于“蜜”的“甜美”“柔和”与“粘连”。理论性的认知可以揭示“甜度”或“黏度”,但无法将人们“拽入”那独特而丰富的感受。在他看来,欣赏艺术也是如此:“艺术品也是要去看的、要去听的,任何的关于艺术品的定义和分析……都不能取代我对此艺术品的直接感知与体验。”因而要从这个角度来定义“沉浸式展览”的话,则这类展览旨在塑造沉浸式的环境,让观赏者更能调动自己的感知能力对艺术品展开探索,进而产生丰富、独特的感受。
事实上,一批较早的“沉浸式艺术”正是秉持了此种思路,这些尝试始于20世纪60至70年代,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如其中一件作品,在美国圣地亚哥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窗户上拆出了三个直通外部的“洞”,它们让博物馆向海岸敞开,使观者能直接感受到光的照射与变幻、海风的吹拂与气味……由此,博物馆空间与整个海岸线相连,成了一整件可供“沉浸”与“感受”的环境艺术品。
近年来,“沉浸式艺术”的商业潜力得到了更多发掘:2020年伦敦蛇形画廊发布的《未来艺术生态系统》报告指出,运用沉浸式艺术,艺术家有可能绕开传统的艺术中介机构,直接向公众出售门票。而对传统策展机构而言,沉浸式艺术使运营者无需再为展品支付昂贵的保费,同时,新媒体的可复制性让此类展览可以在多地运营,从而降低了策展和运输展品的成本与风险。
然而,“沉浸式展览”在当下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有评论者认为“沉浸式展览正在毁灭艺术”。在这些质疑者看来,一些所谓的“沉浸式艺术展”正变得愈发“粗糙”与“同质化”。比如,有国外的评论家曾描述了一次粗糙的“凡·高沉浸展”:“将低分辨率投影仪对准空白画布并不能产生太大的感官刺激……其中我最‘喜欢’的元素是他们对《凡·高在阿尔勒的卧室》的‘忠实再现’。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壮举’,采用了两平方米的油毡地板和一些看着像是从监室偷来的家具。”同时,他认为此类展览已形成“套路”:“投影仪、环绕式音响和令人不舒服的古怪座椅支撑起了这些沉浸式艺术骗局。”
事实上,一旦从本质上界定“沉浸式艺术展”,便不难发现这些糟糕的展览是对“沉浸式艺术”的背离。“沉浸式艺术”原本希望促成观者与艺术品的互动,其之所以令观者“沉浸于”特定环境,正是为了“激活”而非“淹没”其感知,进而引导其完成对艺术作品的“体验”和“亲历”。然而,也有一些策展人似乎简单地将营造奇观、堆砌符号作为布展意图,以产生一种“无深度的强度”:说它们注重强度,是因为巨大的景观、环绕播放的音乐与四处堆砌的符号都将观赏者置于高强度的“刺激”之下;说它缺乏深度,是因为对艺术品的“深度体验”需要的是由在敏锐感知引导下的细腻探索。这种“粗糙”且“同质”的展览并不利于观众真正去理解艺术作品:观赏者无需主动探索就能获得高强度的刺激,可这些杂乱无章的刺激非但无助于激活感知,反而会干扰感知的运作;被符号所簇拥的观众不是因为欣赏艺术、与作品同在而深感满足,而是通过拍照打卡、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点赞,获取某种“满足感”。
事实上,好的“沉浸式艺术”既体现在艺术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心理层面,这已经在一些优秀的展览中得到了实现。
就艺术层面而言,如若布置得当,那么“沉浸式展览”所用的装置就能为观者的感知提供引导性的“语境”。在创作作品时,艺术家常将自身的丰富感知融入其中,展现出作品的鲜活意趣。如法国印象派画家塞尚曾说,“我们当能绘画出树木的气味”。然而,如若只注重小小画幅,那么对于大多数艺术素养并不算出色的观者而言,感知作品难免令人举步维艰。在17到18世纪巴黎和伦敦举办的一些艺术展览上,一些观众就表示感到“被绘画包围……不知所措、心烦意乱,不知道该往哪里看。”这便源于“引导”的缺乏:每一幅作品似乎都展开了一个诱人的世界,但观者却难以求得与其中任何一幅的共鸣。
相比之下,“沉浸式艺术”就可以通过塑造一定的语境来传达艺术家的所感,由此为观者提供引导。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作品“寂静的秋天”:艺术家在展区内设置了一片由机器树木组成的森林,空气中弥漫着植物和森林的香气,而这些机器树木会释放出雾气和气泡,人们可以触摸气泡,甚至戴着特殊的手套把它们抱起来。在这里,树木真正具有了“气味”——装置令艺术家的感知和观者的感知同频共振。对于许多经典作品而言,这种引导性的语境也格外重要。
就社会心理层面而言,“沉浸式艺术”鼓励人们与周遭世界建立“共在”的关系,这有助于打破现代社会中常见的“主客二分”心态——人们要么认为周遭世界与己无关,因而抱持着“冷漠”与“静观”的姿态;要么以“工具理性”的逻辑“宰制”并“操纵”外部事物。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兰登国际的“雨屋”。在“雨屋”之中,观众头顶是一片倾泻着雨幕的天花板。展览空间中设置了摄像头以捕捉观众的位置和身形,而这些数据将被用于操纵“降雨装置”:观众走到哪里,密密麻麻的“暴雨”就会在他身旁驻足。兰登的作品向来以“再现人类与科技间的关系”为母题,“雨屋”正符合这一要旨。一方面,技术的运用将人与“暴风骤雨”隔开;但另一方面,安全的代价则是人的方方面面都被技术所监控和捕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认为技术问题遥远且与己无关,或简单将技术视为手中的工具。但“雨屋”则打破了这种“前反思”的状态,要求人们以富于参与性和反思性的态度面对时刻与我们共在的技术。
“沉浸式艺术展”近年来在国内也颇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尝试,例如国家博物馆的“华彩万象——石窟艺术沉浸体验”、广东美术馆的“未来的触感——沉浸式数字艺术大展”等,它们均有明确且别具匠心的策展思路,旨在“激活”“引导”而非“淹没”观者的感知。同时,它们也力图借“沉浸式”的布置来活化本土艺术与文化资源。正因为这些较为成功的尝试,我们有理由对“沉浸式艺术展”的未来抱有期待——在未来的发展与探索中,这种形式或能对“感知”本身的丰富性做出进一步发掘,并更充分地兑现其艺术与社会潜能。
(作者:谢廷玉,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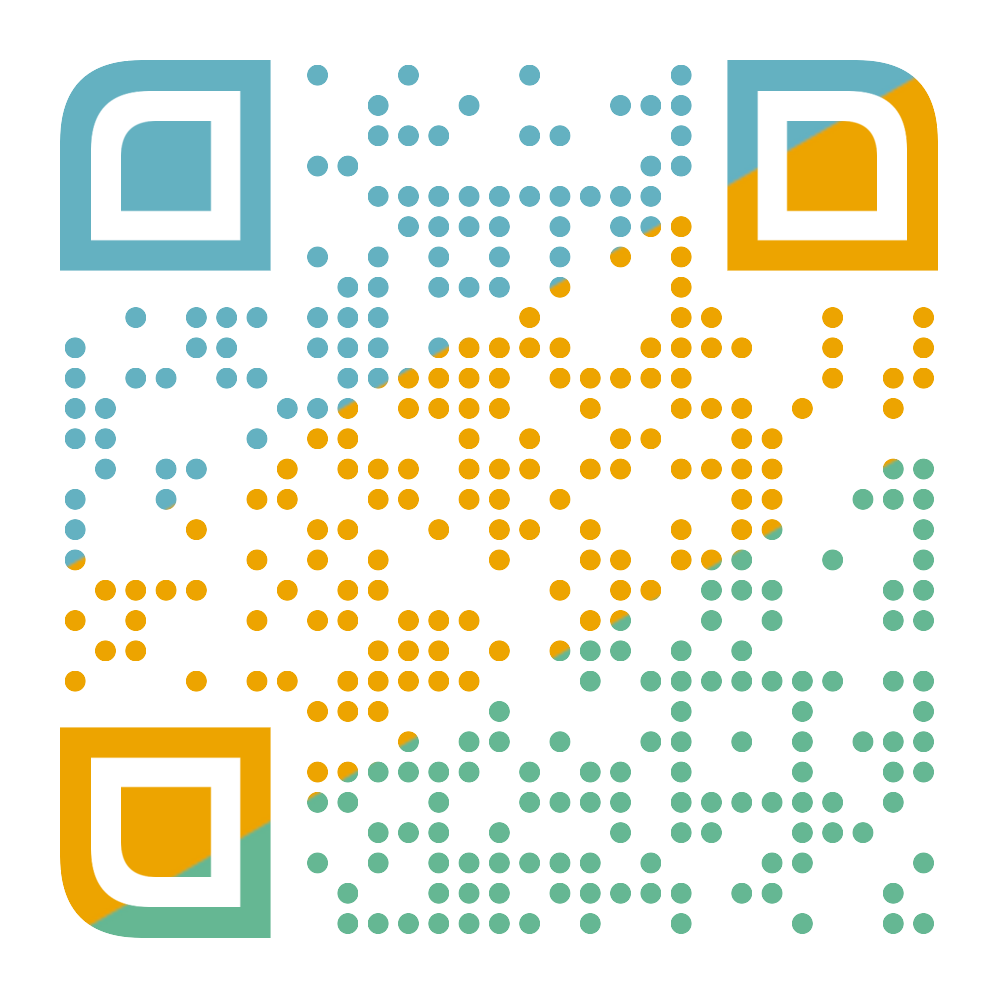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