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文化周末:山远水长三里河
从鲜鱼口东边出来,过马路,闪出一条河——三里河。
河身细溜,浅而多弯。水上架了短桥,由这岸踱到那岸,没几步,不费脚力。桥,有的直,有的曲,衬着河景,来得巧,来得妙。
河不宽,岸道也瘦,平铺大条石,依势盘迂,随处分岔。初来者总要在岔口停住,心里说,曲里拐弯的,奔哪儿才是呀?

北京三里河公园 谌强摄
南北之人喜欢在这片水巷流连,尽把嗓门压低,步子放缓。夹岸巷路,愈显出它的深与幽。
还是贴着水走吧。
春捎着花香来了。绯艳的光色染透榆叶梅的蟠柯,明黄的薄瓣缀满连翘的虬枝。岸柳的新芽抽得鲜,抽得浓,袅袅柔丝在河风的梳理下依依地斜垂,滴落点点翠。芦苇成丛的河边,凉亭、轩榭、石凳、竹栅、花墙、瓦舍、檐下晾晒的衣衫、窗前堆置的杂物,跟池塘中泼剌的锦鲤、凫游的黑天鹅,一并在水光间交映。一户人家门前,有只公鸡在溜达,扬着颈,威风赳赳,我怕它抽冷子放出一声雄啼,惊着谁。鸡栖于埘,鸭戏于水,京城大前门之旁,竟遇此种景致,倒也端量不出同乡下风光有何相差,真用得上《红楼梦》里的那句话:“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李笠翁曰:“筑成小圃近方塘,果易生成菜易长。”这家主人,聊得结庐返耕、抱瓮灌园之乐。
眼底好景,全似照着画意做成。味浓的墨趣,洇开了。
水边光景总是牵情的。河畔小憩,得一身清凉。我定下神,朝粼粼明漪凝眸,很似面向着积水潭的老舍:“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何为松闲?这会儿,我像是明白了。
明面儿上的水,眼光一抛,触着了;瞧不见的水,也是瞒不过人的。流到草厂三条,河水忽然止住了,潴积于石堤下,好像前无去路的样子。逃离人们视线的这泓水,钻进街巷底下了吧,循着故道的走向潜潜而逝,不留一点影。一层厚实的青石板压得那么牢,把脉脉自流的它跟世界隔了开来。
水藏在地下,旧名却未隐去。眼观四近,桥湾、河泊厂、北深沟、芦草园、薛家湾、水道子、金鱼池,还有刘半农提过的“却丢在远远的前门外”的西河沿,不管是胡同、街巷、公园、车站,凡能叫得出的,哪一处不跟水沾边?
刘半农还说,西河沿“当初是漕运的最终停泊点;据清朝中叶人所做的笔记,在当时还是樯桅林立的”。沈从文则在《游二闸》中讲起,“长达十来丈”的运粮大船顺河来去。
“樯桅林立”,成了旧景。时下,这一带就剩下标着“崇文门西河沿”字样的路牌了。说得切近些,我住的板楼,便在河沿跟前。
还有正义路。它的北口正对着南河沿大街。街边的外金水河,又叫“菖蒲河”,所谓“御河”,也是它。河水自玉泉山而下,流来流去,到了南河沿,也到了正义路。敢情这水连着西山呢!真是山远水长。
清末,正义路这一段御河的两岸修了路。傍水而行的人,能隔河相望,又可过桥往来。御河桥,曾有三座,不知哪一年,没了。河床上开了涵洞,挖了暗沟。后来,冲着老天的河道被石板盖严了,地面再无水流。带状平地上辟出植篱芊蔚的街心花园,天一暖,树身着了绿,那个鲜呀!平日,我披着槐荫柏影闲步,仿佛听见了街路下淙淙的水声。踏着浪花的我,心里欢畅吗?那还用说!
早先,出了正义路,御河流入前三门护城河,三里河水有了来处。现今,被条直的路、横贯的街掩去踪迹的御河,大概仍跟三里河在深黯的地底交汇。它们的接力在岁月中悄然进行。
清清之水,源源而至。我不愿它俩断开,也断不开。
三里河有自己的旅程。
这条开凿于明正统年间的小河,或以济漕运,或用于泄水。它北起鲜鱼口,过打磨厂,穿芦草园,越北桥湾,南注金鱼池。这一流,三里地出去了。河长三里,河名据此而出。
这还没完。河水又南去而东折,经十里河奔向张家湾,抵烟墩港并入通惠河。别存一说:三里河出金鱼池,逾红桥,汇至左安门护城河,就是萧太后河,继而东泻龙潭湖,过台湖而达张家湾,径归凉水河。无论通惠河,无论凉水河,一跃身,都算扑进北运河的怀。
照此看,张家湾应是大运河上的重镇。这个地方,因无机缘,未印我的履迹。可我编发过张中行先生的一篇以“同访通县张家湾”为题的散文,可说卧以游之了。张先生伫于明朝万历年间造筑的石桥上,迎风放眼:“桥东西都是河道,今虽水少,形势未变。土名是萧太后运粮河,东通北运河。立在桥头西望,河道相当宽,一直到尽头,名西坡岸,都是卸粮卸货之地。东部的作用一样,总之都是码头。”入他笔底的,应是漕河之上那座辙印深深的通运桥。遍布桥面的沟槽,是刻在运河史上的粗重褶痕。
张先生的原稿,我仍留着。一晃,好些年过去了。
思绪在飞,目光还在这湛湛的河上。我心里也淌着一条河,情感的河,跟它并流。水音中低回,故人、旧友、往事一同涌来,清晰了片时,少顷又模糊了。记起朱自清的话:“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整条河都是绿的,只有锦鳞耀红。枝头歇着几只鸟,背着日光,向着水里,盯无忧的鱼。游鱼自由地摆动半透明的尾鳍,弄着清浅的水,如舞。真也不挂一丝愁。我投食给它们,一小块一小块掰得很细,鱼儿浮上来,嘴一张,吞下了。
水岸一片安静。时间慢下来,不像在北边的前门东大街上那般追风逐电。
这是三里河的况味。
河史既古,景致又好,兴筑之举也就不少。况且在城南,胡同代那些堙废的河道沟渠而起,衰去的风物倏尔活了。河流故道,换了面貌。
晚近,老房旧屋,着力缮葺,看上去精整,过门不知谁人宅舍。这里地段棒,又能远市肆喧响而近田舍风致。择此定居,晨起推窗,目迎水光树色,己身仿若入画中;清夜,淡白的月华落下,河面好似凝了一层霜,倚枕的人便是醒着,宛然已在梦里了。
桃源之乐占满了心。这样的日子,过得美!
青云胡同把口儿,立着一个宅子,高墙深院,不寻常。梅兰芳住过的。
显目的一景,是会馆。年深月久,投止之所皆成旧院。有些找不着了,空留一串名儿。残而未圮的会馆咋样了?这不,正照着当初的形制动土木呢。长巷头条里,几个建筑工人卸下一车一车的石子、沙土、方砖、钢筋,往当院堆着,码着,摞着,紧忙活。
迈过一段木板搭出的步道,前头路侧,会馆接得密,门面也修得新,完竣了。我抬眼一瞧:汀州会馆、泾县会馆、新建会馆、丰城会馆……真够热闹的。
从前的会馆,多是南方人开的。开了一家,又开一家,在前门之下连成片。他们把水乡气息引到了京城。青砖灰瓦的四合院盈着水汽,湿漉漉的。
入京赶考、经商的外省人,也会对河岸景物留下记忆,并将它们带向远方。
友人李存修是一位旅行家,古稀之年,背上行囊,沿大运河而走,访风问俗,采摭至详。返家门,他把风雨行途中的所获写下来,笔一摇,三十多万字,了不得!对他的这次远足,我很为佩服。运河闻识,我固浅陋,还是给他的这本《行走大运河》作了序。提笔的那刻,神思生了翅,朝南而翔。
我是办报的。有一阵儿,为一个对话栏目而忙,“中国大运河保护与联合申遗”恰是一个好选题。那次访谈,舒乙先生的一番话,叫我弄清了大运河的定义。他说,申遗的项目不叫“京杭大运河”,而叫“中国大运河”,因其包括三部分: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江南运河网。此言凿凿,确可信据。我的眼界宽多了,所思也更深。恍兮惚兮,吴王夫差、隋炀帝的身影,在水浪间浮了上来。
又过风了,软软的,河面起了皱,鳞波间的阳光抖成了碎片。我靠着桥栏,看水,观鱼,赏花,听鸟,心如一朵云。若能坐入颜料会馆,让京昆腔曲悠悠绕耳,则可将另一种逸致领受。
莹澈的三里河,缓缓地淌,荡出的清涟融入运河的汤汤之水,也连向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浩波,一路奔腾,跟绵袤流域内的平畴沃野相逢。
河虽小,气象却是大的。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26日 15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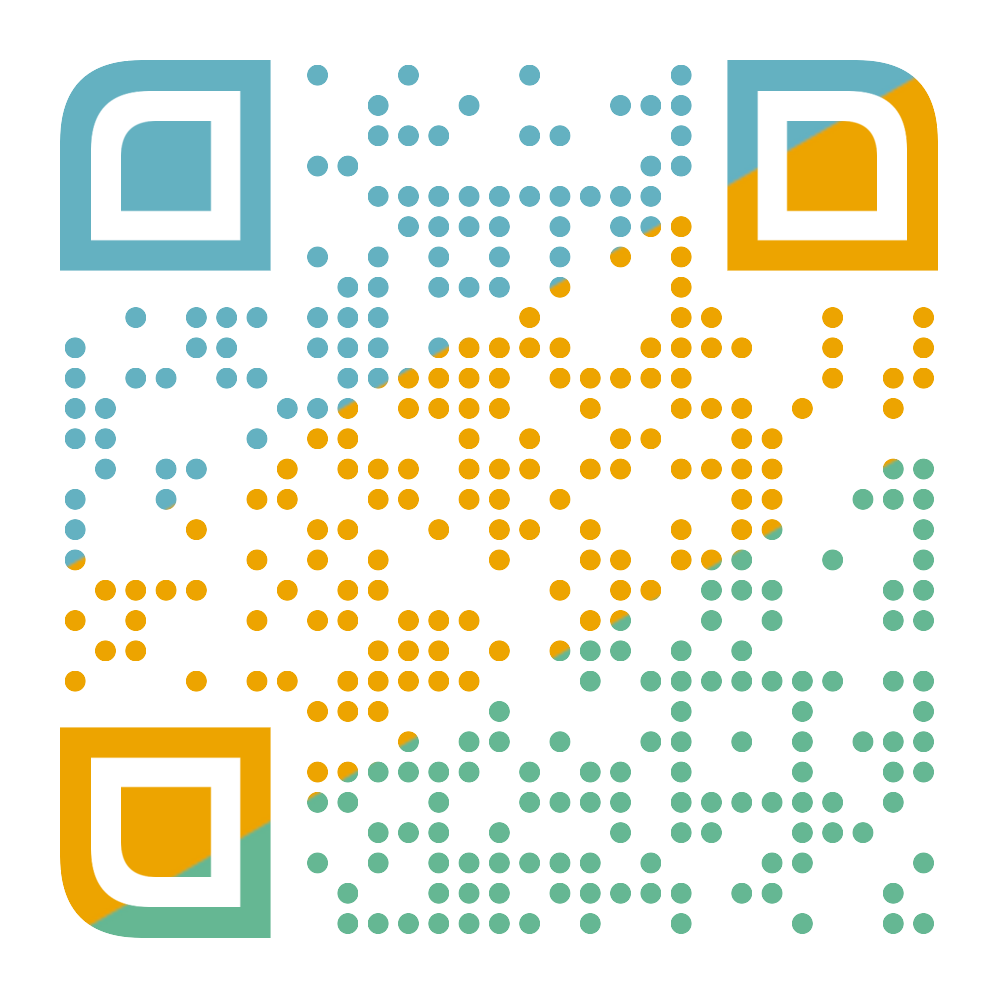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