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中国式推进
王南湜
《光明日报》( 2024年02月26日 15版)
马克思哲学革命,作为人类思想领域的重要变革,主要表现为“关键词”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换。但改变世界不是不要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解释世界”的方式,即转变为一种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这一改变的革命性在于将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作为“解释世界”之终极根据的“理念”“存在”“上帝”“绝对精神”之类超验存在物“打回原形”,拉回到现实世界,取消其神圣超验性。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相反,中国传统哲学从根本上据守着现实生活世界的实在性。这便意味着马克思哲学革命指向的目标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根本点上具有某种“高度的契合性”,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便是在与中国传统哲学汇通的基础上的一种中国式推进,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是“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层历史意义,正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才得以充分彰显。“第二个结合”在某种意义上乃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种中国式推进。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源
马克思之所以将以往的哲学归结为“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正缘于以往的哲学否认现实世界自身的直接实在性,而将之视为某种永恒的超验存在物的派生物,而这种超验存在既然是永恒的实在性之物,那么便是不可改变的。因此,要确立“改变世界”为新哲学之目的,便须首先确立现实世界的直接实在性。于是,哲学革命的首要任务便是摧毁西方形而上学的超验存在物之设定,将实在性交还于现实世界。与之相关,既往哲学中这一超验存在物设定得以成立的关键,又在于或隐或现地设定了一个无限的或绝对的超验主体,以之作为其认识论前提,因而摧毁超验存在物必须同时否定绝对的超验主体之存在。而这一否定又意味着将这一虚构的无限的绝对主体转换为有限的人类主体。如所周知,这一向有限主体的转换是从康德开始的,但康德的这一转换极不彻底,只是形成了一种理论上不能令人满意的二元论体系,而嗣后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对这一二元论的克服,却又导向了一种超验形而上学的“复辟”。只有马克思在反击这一“复辟”的“再革命”中,才真正将康德所开启的摧毁形而上学超验存在物的革命推向了彻底。
康德的哲学革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自对现代世界的深刻洞察。他看到了不同于古代及中世纪个人对城邦、庄园、行会、教会的从属,在现代世界中随着这些传统共同体组织的解体或改变,“人”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个体。这种个体的人只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而不再被许诺能够通达无限的超验存在物。于是,与古代及中世纪将“理念”“上帝”等超验存在物置于哲学的关注中心不同,“人”这种有限的存在物,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据此,康德径直提出了“人是什么”这一现代哲学的根本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当做什么?(3)我可以期待什么?(4)人是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学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将目光转向人,追问“人是什么”不仅意味着现代哲学不再沉迷于从神或抽象的理性看世界,而是开始以作为现实存在的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及自身,而且这里的“人”也不再是作为共同体之某种样本 的“人”,而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个体之人。康德的这一革命性转向亦可称之为人类学转向。
但康德的二元论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是基于现象与物自身的二元分割,将知识限定在现象界,难以说明知识的客观性;二是将人理解为孤立的抽象个人,将社会国家理解为契约性构成,难以说明现实社会国家的历史性特征。这导致了从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德国观念论对其二元论的批判与克服。德国观念论者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和社会国家通过人的活动的生成性,虽然能够较之契约论更好地说明社会国家的有机性、历史性,但却无以说明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且其对于社会国家之有机历史性的说明亦是基于超验主体性进行的,因而也是极其抽象的。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其积极意义,但亦认为这是对于“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一种“复辟”。由于康德批判哲学亦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故而这一复辟便亦是对于康德人类学转向的反动。因此,尽管这是一场“富有内容的复辟”,马克思仍然坚持要推进康德对于超验形而上学的批判,而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思辨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将其斥之为:“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使外化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显而易见,这种自拘于抽象的思想世界的主体活动是不可能执行实际地改变世界的行动的,因而必须将之“还原”,以发现真实的主体。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针对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超验的绝对主体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人是对象性活动”的革命性命题。这一命题的核心要点是“对象性”与“活动”。“对象性”所针对的正是黑格尔的超验的“绝对主体”。与“绝对主体”作为“唯一的存在物……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的“无对”相反,现实的主体乃是“相对”或“有对”的“对象性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但仅仅指出这是“主词和宾词”之间关系的“相互颠倒”尚不足以驳倒这一“颠倒”,而是必须阐明这种“颠倒”是如何产生的,方能真正使之“原形毕露”,破除其超验神秘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尚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思辨性思维方式,其时的“对象性活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之过程,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审美性劳动”,而非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因而此时的“人”便仍未达到“现实中的人”,也就仍不足以解决这一“颠倒”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当马克思将劳动理解为生产满足人们“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之时,这一“颠倒”问题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野。这便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就全然道破了统治西方思想两千年之久的超验形而上学之实质,将西方形而上学所持守的超验存在物彻底“打回原形”,将被颠倒了的“主词和宾词”关系再“颠倒”了过来,将康德的不彻底的人类学转向推向了彻底。于是,人类“周围的感性世界”便只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而非某种抽象的超验存在物的显现。这样一种从人类活动或“行事”看世界的视域,乃是一种“事”的世界观或本体论。
马克思哲学精神的中国式接续与发展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既然是以改变世界为目的,那么这一革命便不能只运行于思想观念领域之中,而必然要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方能接续与发展。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直接投身于改变资本主义的实践之中,而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则更是对于这一革命的现实推进。但在这一实践推进中,马克思所实现的彻底的人类学转向却未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阐释,而是出现了两种偏向:一是第二国际和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机械决定论的旧唯物主义阐释;二是以卢卡奇为典范的黑格尔主义的解读。这两种阐释之偏,就在于都以不同方式诉诸了某种超验存在物,从而都不同程度地背离了马克思的彻底的人类学转向之初衷。而唯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展出了一种与马克思所开创的彻底的人类学转向具有深刻契合性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论著之中。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其极富特色的哲学思想不仅在《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论著中得到了集中阐发,更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政治、军事论著中得到了极其精彩的表达与发挥。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的现实的改变世界的能动性哲学精神之深刻把握,充分体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一段话中:“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如果我们把这段话中的“军事家”主体一般化为现实活动中的人,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的命题加以对比的话,便不难看出其间本质上的高度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意味着,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把握住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何以能够如此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呢?答案便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中国传统哲学之“事”的世界观的“前见”或“底色”。这一“事”的世界观便是最初表达于《易传》之中的“三才之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这一对人在天地之间能动作用的强调,在《中庸》中有着更为明确的表达:“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一以“人道”而“赞”“参”天地之道的“三才之道”,周汝昌先生将之盛赞为:“人参天地,共为三才——这是中华文化思想的一大总纲。”毛泽东同志运用他基于中国哲学的“底色”所把握的马克思哲学真精神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
在“第二个结合”中彰显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层历史意义
处在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的当代中国,亟需能够切中中国与世界现实需要的新思想新理论,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因而,作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是时代的呼唤,呼唤着由之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样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便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巨大推进。
“第二个结合”的深远历史意义,可从必要性与发展前景两个方面去理解。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高度的契合性”提供了两者有机结合的思想前提或可能性,而在现实历史中,这一结合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达一个多世纪反复探索和创造性实践的结果。这一持续不懈的探索意味着这一结合必定从根本上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首先,作为最具先进性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仅给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更新机遇,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历史最为悠久的非西方文化的国度中实现创新发展提供了最为广阔的历史机遇。因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从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近代历史进程来看,正是自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形态,在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一种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特征,又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
其次,“‘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随着历史的进展,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强大支撑。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高度的契合性”,则正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通过“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具有深厚的中国底色,从而也才能够以其数千年积淀之历史力量“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再次,“‘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马克思主义作为源自西方文化的最先进的思想体系,与具有数千年之深厚底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使得中华文化达成现代文化,同时亦使得源自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积淀的文明的深茂根系的营养支持,从而必然形成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最后,“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进入现代世界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使得国人一度失却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使得国人重新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权,重获文化自信,从而必将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重展中华民族的历史盛景。
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的根本目标是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表述中的主词“文化生命体”有“有机统一的”和“新的”两个限定词,因而理解这一目标的关键便是这两个限定词。“新的”作为“文化生命体”的限定词,意味着这一目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的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性建构。而现代性的一个本质规定乃是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活之中的决定性力量,因而,作为民族文化之核心的哲学精神的现代建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将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纳入自身,将自身转变为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存在形态。但这种“纳入”不能是黑格尔的那种通过将哲学拔高为超验的“理性”,而将科学贬低为经验性的“知性”的方式去进行。因为经由这种方式形成的“文化生命体”并非真正“有机统一的”,而是充斥着内在的紧张与冲突。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一边是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另一边则是不绝于耳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激烈批判,这便是上述那种内在冲突之明证。这一进路之所以无法避免失败之结局,归根到底在于其形而上学之“超验”与“经验”之二元论设定。而马克思彻底的人类学转向将形而上学的超验存在物拉回到了现实世界。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科学乃是通过将现实世界的某些规定性抽离出来构成一种简化了的理论模型来加以把握,以便从中发现更为有效的改变世界的方式方法。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建构的一个关键环节,便必然是建构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科学(特别是科学思维方式)的关系。由于马克思彻底的人类学转向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因而以马克思的科学观为典范而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现代科学观,当为合理可行之事。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事”的世界观经历两千多年之发展,具有更为深厚的思想积聚,从而经由现代阐释发挥的中国传统哲学当能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更大的有益引导与支持。
与科学观的现代建构相关,中国哲学精神的现代建构更为根本的乃是价值理想的塑造。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所存在的“高度的契合性”,乃是实现两者有机结合的前提;但中国传统哲学毕竟是与传统社会相匹配的观念形态,而当代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则是匹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因而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予以建构。一个社会的价值理想并非凌空蹈虚之物,而是必定要灌注于现实生活之中,实际地引领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因此,价值理想要想起到实际的引领作用,就必须立足具体实际,为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而有效的价值引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具有超越西方现代文化的特质。一种文化最核心的是其价值理想。西方文化价值理想的根本特征乃是指向一种超验的理念世界或上帝的天国世界。而马克思主义自由王国与中国儒家的大同世界,其根本特征都是一种现实世界的理想状态,而非超验之存在。超验的价值理想,由于其绝对的理想性一般难以兼容与之不同的价值理想,因而当其面对现实世界中的价值理想纷争时,便难于提供合理的处理方式。而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现实性价值理想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则能够为纷争不已的现代世界提供一种更为合理的价值理想。更重要的是以这种价值理想为目标去探寻解决中国和世界发展中的问题,所形成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制度与准则,亦可形成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可以为现代世界的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都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强调“行可兼知”,“解释世界”对于“改变世界”的从属性。由两者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文化便必定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相携而行的。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也必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成功,从而也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种中国式推进。
(作者:王南湜,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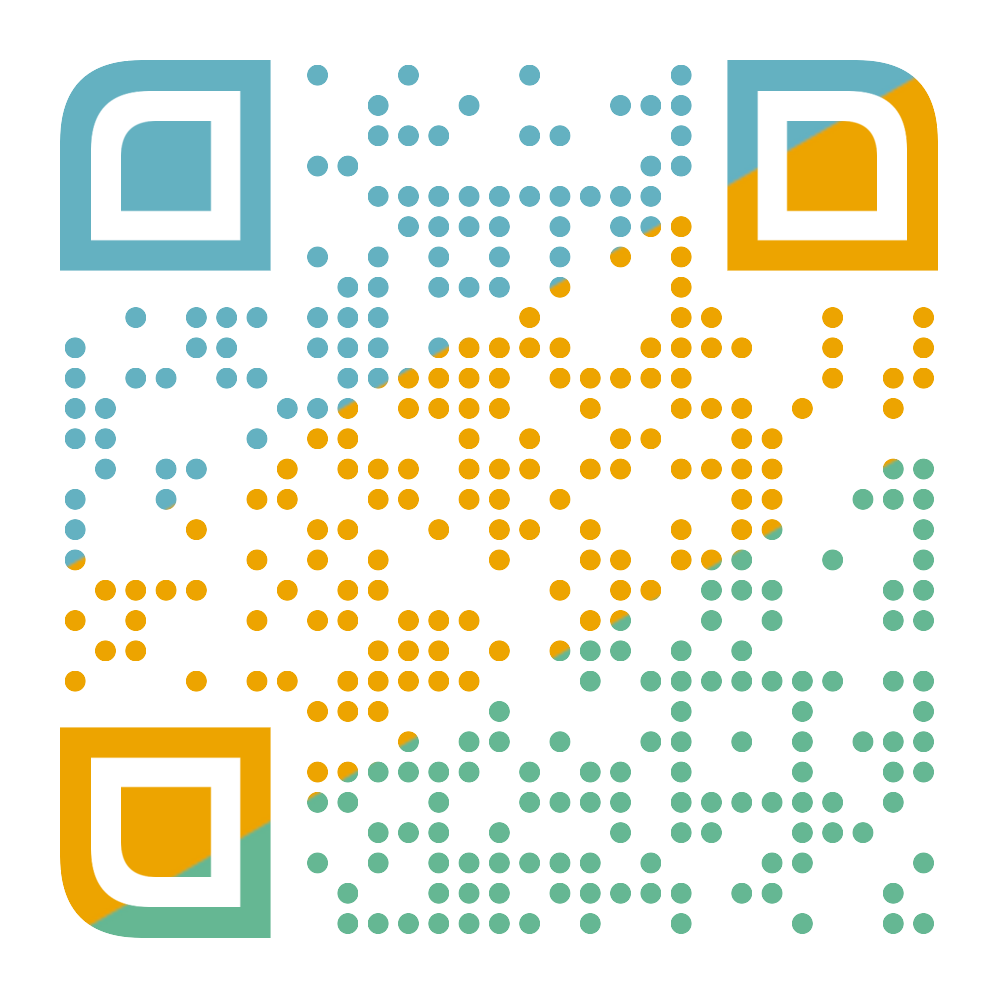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