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语言研究的“植树人”
王春辉 田列朋
《光明日报》( 2024年02月26日 11版)

学人小传
李宇明,1955年生于河南泌阳。语言学家,中国辞书学会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81年本科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1984年硕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现代汉语专业。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著有《儿童语言的发展》《语法研究录》《汉语量范畴研究》《中国语言规划论》《中国语言规划续论》《中国语言规划三论》《人生初年》《语言小品文》等著作。主编《全球华语大词典》《语言扶贫问题研究》(两辑)《应急语言问题研究》等。作者供图

作者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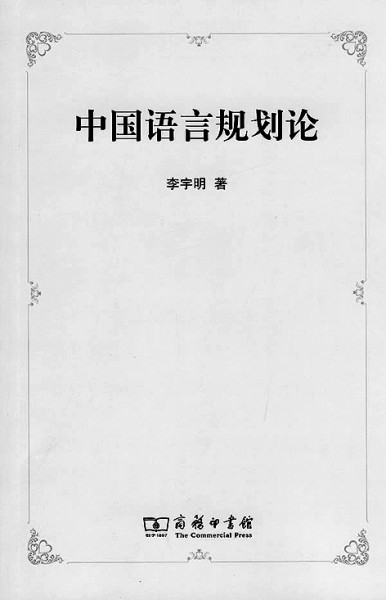
作者供图

1982年,邢福义(前排中)与他指导的第一届研究生合影,后排左一为李宇明。作者供图
【求索】
“语言处处有景观,达意表情传信澜。住院岂只添医理,问学就在自身边。”这是李宇明教授去年年底腰椎间盘手术住院期间的诗作之一。其实腰疾已困扰他25年之久,但他“总舍不得时间去治疗”。就是这挤出来的住院时间,他还在充满好奇地观察着“语言景观”:医院各诊疗区是如何命名的?各种标识用语是否准确?人们如何称呼医生、护士……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但总有人去拓展时光的宽度、挖掘时间的深度。20世纪90年代,曾有记者问李宇明如何分配时间,他说:“我就像是计算机的硬盘,有C、D、E三个区。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打开C盘专心做好行政工作;晚上启动D盘,看点书,做点科研;星期六、星期日运行E盘,指导研究生、访问学者的学习与研究。”近30年,李宇明的C盘从武汉迁至北京,由高校转到机关,再转回高校,功成身退;E盘则是年年岁岁“师相似”,岁岁年年“生不同”,退休而息;唯有D盘,几十年如一日,无退无休。
对李宇明来说,学术不仅是追求,更是一种信仰。他说:“也许有人借学术来谋稻粱、谋功名,一旦稻粱足、功名得,或一旦学术不能谋得稻粱、功名,便会将学术弃若破履烂衫。对于我,学术只是探讨世界之谜的一种特殊嗜好,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今专叩语言门”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李宇明考入郑州大学,被编入中文系三班。和很多中文系的学生一样,李宇明也有过“文学梦”,不过,他后来主动选择了语言学,这与当时郑州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教师、课程、氛围等密切相关。
当时的郑州大学中文系,集聚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教师,如张静、张桁、李法白、许梦麟、刘镜芙、柴春华、崔灿等先生。张静先生当时正组织全国语言学界的力量编写《现代汉语》教材,触及层次分析法等当时的学术前沿;周庆生先生教授音位学理论;厦门大学黄典诚先生到郑大讲学,提供了调值听辨力和国际音标的知识给养。李法白先生当时开设了一门选修课,有一次上课,他列举了先秦汉语中的10余个词头,并提出“这些词头应各有作用,只是它们的不同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各有作用”“没有认识到”,这引发了李宇明的研究兴趣,遂研读论著、搜集例句,他撰写的《所谓名词词头“有”新议》在《中州学刊》刊出,提出名词词头“有”是表特指的指示词的新论,其语法作用是加在名词之前将泛指变为特指。
这篇论文的发表及张静等先生的肯定,鼓励着李宇明继续探索。“仿佛翻越了一座座山丘跨入了无人区,又像蹚过一条小溪一步一步靠近大海。”1981年年底,李宇明应届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师从邢福义先生攻读研究生学位。这标志着李宇明从“文学梦”中自觉醒来,“而今专叩语言门”。
语言学界素有“南邢北陆”之誉,“北陆”指北京大学陆俭明先生,“南邢”指的就是邢福义先生。作为“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邢先生的研究体大精深、细大不捐。李宇明把邢先生的研究之“道”概括为“尊重语言事实,理论植根于泥土”“每一个领域都可以有不同的‘术’,但都离不开研究的‘道’”。大师引路,汉语语法学自然成了李宇明学术研究的起点。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时间,李宇明的语法研究可谓遍地寻宝、多点开花,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收入《语法研究录》一书中。其中,对非谓形容词的研究,就很能代表李宇明语法研究的特点。学界把“小型”“慢性”“现行”“亲生”“上好”这类词称为非谓形容词,其基本的语义功能是表示事物的属性。吕叔湘、饶长溶曾归纳非谓形容词的几个语法特征,比如,可以直接修饰名词(“小型水库”);可以加“的”用在“是”字后面(“这个水库是小型的”);不能做谓语;不能在前边加“不”或“很”。不过,对于非谓形容词与名词、形容词、动词的种种不同和联系,学界一直缺乏明确认识和深入研究。在《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一文中,李宇明用连续性的观念,在定语的范围内,就空间、程度、时间三个维度考察非谓形容词与名词、一般形容词、动词等的差异与联系。比如,“木头”是名词,“木质”是非谓形容词,二者作定语修饰“家具”组成“木头家具”“木质家具”时,无论在表义还是在语法功能上,都没有多大差别。但是,“木头”在其他情况下可以恢复其空间性,即可以有一般名词的用法,而“木质”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表属性,属性意义比名词更为显豁。一些名词后面加上“式、型、性”等标记之后,就成了非谓形容词,如“中式”“椭圆型”“经典性”等。通过一系列研究,李宇明发现,非谓形容词的地位处在名、形、动三大词类的临接点上,此种地位造成了非谓形容词的高能产性、功能的易游移性等特点。在《语法研究录》的后记中,他写道:“是集也,隐蕴着尚学重道之心迹,记录着语法探索之履痕,故以研究录名之。”邢福义先生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说,《语法研究录》录下了李宇明“20年来走过的语法研究之路”,录下了他“在研究路上留下的鲜明脚印”。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李宇明开始聚焦于“量范畴”这一特定句法语义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在2000年出版了《汉语量范畴研究》一书。他在书中写道:“‘量’是人们认知世界、把握世界和表述世界的重要范畴。在人们的认知世界中,事物(包括人、动物)、事件、性状等无不含有‘量’的因素。例如,事物含有几何量和数量等因素,事件含有动作量和时间量等因素,性状含有量级等因素。人们把握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量’,对于客观的事物、事件、性状等等,人们习惯用‘量’来丈量测算,于是便有了日趋精密的数学和各种测量工具。当代社会更是希望把一切能量化的东西都进行量化处理,在量化的基础上定性。客观世界这些量的因素和各种量化处理的工具与方式,集合起来便构成了‘量’这种反映客观世界的认知范畴。‘量’这种认知范畴投射到语言中,即通过‘语言化’形成语言世界的量范畴。”此书是学界首次对“量”这一句法语义范畴的系统性考察,涵盖了物量、空间量、时间量、动作量、级次量、语势这六类量的次范畴,还归纳出明量/暗量、实量/虚量、确量/约量、客观量/主观量几组对立的次范畴,具有以往学界所论的“数量”范畴所不及的覆盖率和渗透性。
汉语语法研究是李宇明学术研究的第一站,为他后来的学术转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拓荒儿童语言学
1981年,在李宇明接到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并“计划着大展宏图”的时候,他的未婚妻白丰兰“却躺倒在病床上,忍受着被人称作‘死不了的癌症’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折磨”,后来竟生活不能自理。李宇明回忆,白女士“怕成为我一生的拖累,竟给我写了一封绝交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983年元旦,李宇明星夜从武汉赶到信阳市中医院一间病房的病床前,“似一个专横的将军,武断、草率而又郑重地同她在病床上举行了别致的婚礼”。1985年1月,作为对这个“不幸家庭”的补偿,上天给了他们一个聪明美丽的小公主,冬冬出生了。
一方面是家庭的责任与现实的困顿,另一方面是对研究的向往和对理想的憧憬,如何抉择?为了更好地照顾妻子和孩子,也为了让夫人更多地融入社会生活与学术活动,李宇明决定邀请夫人与他一起投入儿童语言学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幼年的语言习得问题已经得到国际学界关注,比如皮亚杰的认知心理视角、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视角,但是这一论题在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片处女之地。开拓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易事。学科知识的拓展与整合,国外文献的搜集与分析,开荒拓土的坚定信念,缺一不可,但更现实的问题是,语料从何而来?
2019年,《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出版了。此书就是李宇明多年前研究儿童语言学的语料。三卷本、一百多万言,完整记录了女儿冬冬从出生到6岁半的语言习得过程和行为。
一个本子一支笔,终年放在常年卧床的白丰兰枕边。每当冬冬有咿呀儿语或之后的连词成句,她总会在第一时间用已近变形的手拿起纸笔,认真记下。有时候,彻骨的疼痛让她实在无法握笔,只能疼痛之后再写下来。多少次,冬冬都是学术研讨会上那个最小的听众。李宇明或抱或领,女儿说的话,他都会即时记下。虽有一个老旧录音机可用,可以先把声音录下来再转记,但有过转录经验的人都知道,反复倒带辨别声音,更费时费力。夜深了,李宇明进入自制的“小书屋”(斗室之中,为不影响妻女休息而搭起的不透光的围挡),整理白天记录的冬冬语料,看文献、写文章。在纸与笔的时代,从来没有一份儿童语言成长的记录能如《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这般,持续了六年半,记录了上百万言。
正是基于这些语料,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李宇明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的处女地里辛勤耕耘。他和他的家庭也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和满满的爱意:白女士在李宇明的鼓励下,变得积极乐观了;李宇明出版了6本相关专著(其中一本是和白女士合著的《父母语言艺术》),发表了40余篇儿童语言习得个案研究及相关论题的论文,成为中国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的拓荒者和领军人。
有同事曾开玩笑说,李宇明从讲师晋升到教授屡次破格,其中有一半是女儿的功劳。虽是谈笑,但是每个人都明白在这累累硕果背后李宇明和夫人的艰辛付出。这份研究是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在驱动,是“与家事俱进”的成功。
20余年后的2019年,李宇明“重操旧业”,开始进行“中国学前儿童语料库建设及运作研究”。此时,他对这门学问有了新的认识:第一,儿童语料是儿童语言研究的基础,但是收集困难,需要建立专门的语料库实现学术共享。第二,未来是为各行业各人群配备人工智能(AI)助手的时代,儿童玩伴、“智能妈妈”的配备需要改变儿童语料的收集方法,需要让计算机理解儿童语言,因此需要建设新型的儿童语料库。第三,儿童语言研究应是“为儿童的”,要研究社会上的“涉儿人群”如父母、幼教、儿科医生,以及儿童精神产品、信息化产品和其他各种用品的生产者对儿童的影响,并为他们提供儿童语言学的学术支撑。
新认识就是新的学术使命,儿童语言研究与智能化、与社会相关人群的结合,必将展现一片美丽的学术风景。
用脚和心做学问
2000年年底,李宇明调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同时担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此后的工作和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工作发展到哪儿,书就看到哪儿,文章就写到哪儿,为工作而学习。”行政工作占去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也给他创造了学术研究的新天地。此前,李宇明的部分研究也涉及语言应用、语言规划等问题,但都只是浅尝辄止。从2001年开始,因工作需要,他开始潜心研究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治理。
“矿产资源”“人力资源”“旅游资源”这些概念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作为语言学家,李宇明积极倡导“语言资源”的理念,强调真正认识语言的资源意义,特别是把语言资源作为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理念,并在国家层面、在全国范围开展语言资源保护行动。从2004年开始,国家语委先后设立了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和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用大规模动态流通语料库来监测语言生活状况,举办“汉语盘点”活动,编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系列皮书。2006年,在时任国家语委主任赵沁平的支持下,李宇明提出了进行全国语言普查的构想,并在曹志耘、张振兴、刘丹青、孙茂松、徐大明、乔全生等学者的支持下,开始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准备工作,2008年该项目正式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来录音录像,建立了统一的调查、记录、建库、复查等标准,标志着语言调查技术进入新阶段。近20年来,以这些实践为基础,学界产出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学科化进程也已开启。近些年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也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2018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长沙联合召开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会上发表的《岳麓宣言》大量吸收了中国语言保护的成果。“语言资源”不仅是中国语言规划的重要理念,也成为国际语言规划领域的公共产品。
李宇明重视从宏观视野看中文,他的研究广涉国际中文教育、华文教育、国家语言能力、中文的国际传播等领域。除了与张西平教授合作主编“世界汉语教育丛书”“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最近几年,他又围绕海外汉语学习者的低龄化、汉语的外语角色、国际语言传播机构发展历史与趋势等诸多论题著文立说。他也是《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策划和主编。这两部词典的编写和出版,体现着陆俭明、李宇明、郭熙等一批中国学人及周清海等海外学者倡导的“大华语”理念。“大华语”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大华语”之“大”,是范围意义上的“大”,也就是“全球”的意思。在“华语”前加一“大”字,既是为了避免“华语”指称上的歧义,也是强调看待华语的全球视角、全球意识,强调一种“新华语观”。这种新的观念,把世界华人在共同语基础上连接在一起,且能够引发一系列学术研究新课题,促成语言活动的新实践。
李宇明是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的最早提出者和研究者。他在《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把“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主要包括:一、语种能力;二、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三、公民语言能力;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五、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随后,他又专门针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语言能力需要终身培育、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政策、应急语言能力、树立“外语生活”意识、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的关系等众多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不少学者都积极参加语言能力研究,使之成为当前中国语言学的一大亮色。
2008年汶川地震后,陈章太、李宇明等学者提出了“灾难语言学”的课题,并在李宇明主编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8)》中编入了《地震灾后心理援助用语》一文;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后,应急语言服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1)》刊发了《青海玉树救灾中的语言障碍与语言援助》,不断搜集资料,研究国内外情况,探讨应急语言服务的问题。从2020年起,中国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理论端,李宇明组织编写了《应急语言问题研究》文集,其主编的《语言战略研究》杂志接连刊发了多期“应急语言研究”专题,其他杂志也纷纷设置专栏,带起了应急语言研究的热点;实践端,2022年4月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成立,2023年10月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在四川组织开展了特大地震灾害应急语言服务首次试点演练。
在李宇明看来,语言与贫困具有相关性,因为语言与教育、信息和信息技术等都有密切关系。村村通公路,这是现实之路;户户通广播电视,宽带网络广覆盖,这是电信之路;与此同时也应修筑起宽阔的语言大道,这是负载知识和机遇的大道。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修筑起脱贫的语言大道,就能为改变经济劣势和发展劣势、促进当地社会的文明进步贡献“语言之力”。李宇明认为,中国已消除了绝对贫困,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学术界需要全面研究农村语言生活,建立“农村语言学”;有关部门需要做好农村语言生活规划,特别是面向农村新职业新产业的语言能力建设;各地应建设当地语言文化博物馆,用融媒体重编各县方言志,让传统语言生活嬗变为新农村的语言生活。由周洪波主持,李宇明、郭熙作为主要专家的国家语委重大课题“语言文字事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和举措研究”,目前就正在对若干乡村样本点进行细致观察与描写。他们带领团队重走当年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研究之路,“用脚和心做学问”,脚踏大地,胸燃炽情,将中国乡村的语言现状进行真实的学术呈现,更通过语言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语言任务,有不同的语言生活,语言健康问题始终伴随着人的一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李宇明就关注语言与健康的问题,主编出版了《聋儿语言康复教程》,刊发《聋儿语言康复与言语行为模式》《聋儿语言康复的目标、原则及其有关问题》《聋童声母获得状况研究》《汉族聋童语音发展的规律及康复对策》等论文,还担任湖北省聋儿康复中心专家顾问。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有人开始关注老年语言能力的衰退问题,讨论较多的是开口忘词、语法错误有所增加、说话容易偏题等明显的语言老化现象。李宇明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老年群体的语言现象,致力于推进中国老年语言学的建立,帮助老年人过好老年语言生活。他指导刘楚群做《老年人口语非流利现象研究》的博士后课题研究,与同济大学老龄语言与看护研究中心保持密切联系,在《语言战略研究》组织了两期老年语言学的专题研究,分别由顾曰国、石定栩教授做专题主持人。
在李宇明的倡导和引领下,围绕着上述研究,也伴随着“语言生活四大皮书”(《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言文字政策研究发展报告》)以及语言政策与规划相关期刊的出版,一个具有明确学术追求、具有中国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的学术群体逐渐形成了,被学界称为“语言生活派”。李宇明将语言生活定义为“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这一批学者把语言生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处,努力解决语言生活中的问题,提升语言生活质量。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一批新概念,展现了一系列新的语言观、研究理念和研究视角,发表了一批有针对性的调查和资政报告,丰富了中国社会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打造了一支有共同理想信念的人才队伍。李宇明认为,以“语言生活派”为底盘的中国语言规划已经形成了六大理念: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促进社会沟通无障碍、提升公民和国家语言能力、全面开展语言服务、保护开发语言资源、发掘弘扬语言文明。
谈及自己学术的两次转向和三大领域时,李宇明曾说:“没有语言本体研究、语言理论研究的基础,也很难搞好应用研究;没有学术研究的支撑,行政工作也难以做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工作与学习、研究是有相关性的,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
上郑州大学前,李宇明曾经在河南省汝南园林学校学习过,后来,他常将自己的研究比喻为种树:解决语言研究的一个问题、开拓语言研究的一个领域,就好比是种植一棵树,年年种植,坚持种植,纵有旱涝病害,也会栽出片片树林,最终使之成为守护大地的绿洲。
李宇明重视学术的实践品格,用语言学解决学科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发挥“语言之用”,追求“语言之善”。他曾经在机关和高校做管理工作,但他始终是一位学者,是一位心怀家国、以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语言问题为己任的学者,是一位中国语言学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植树人”。
语言通心,教育向善;学术无价,家国有情!
(作者:王春辉,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列朋,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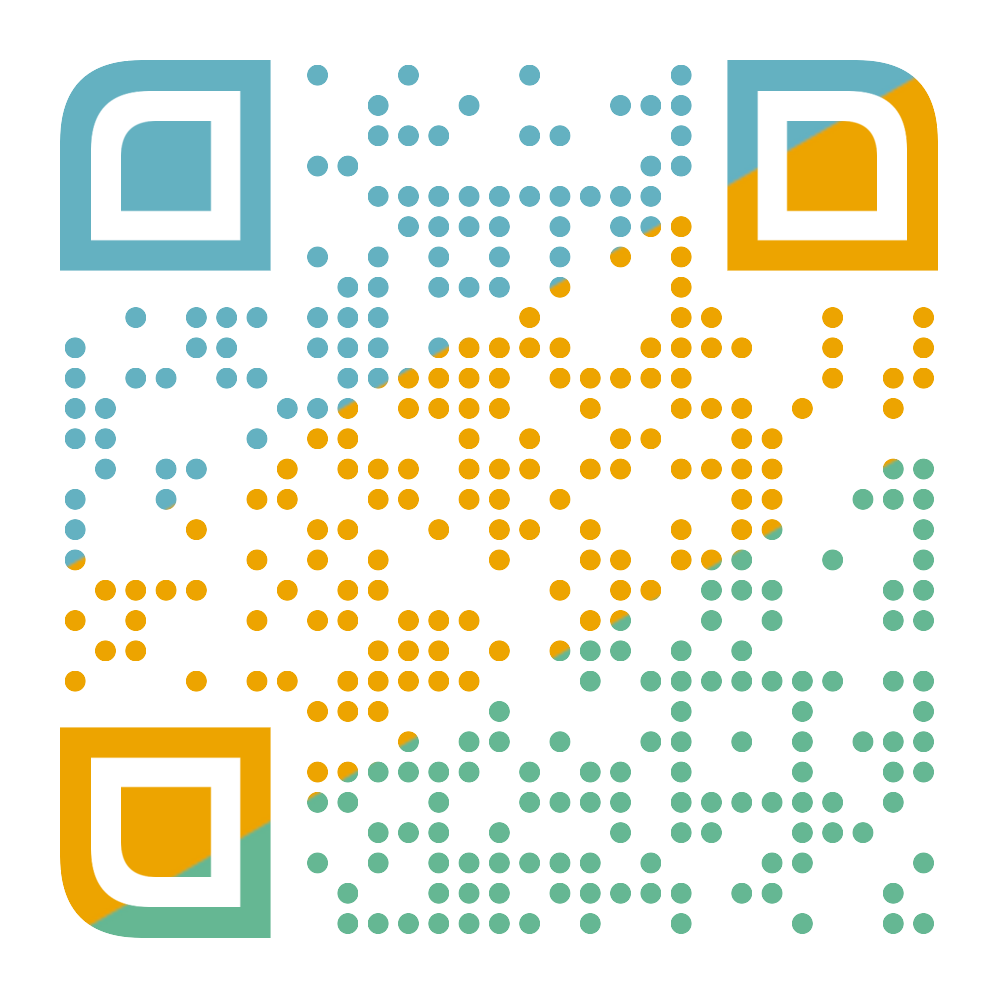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