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司马迁的知音 ——张大可与《史记》
丁波
《光明日报》( 2024年07月29日 11版)

丁波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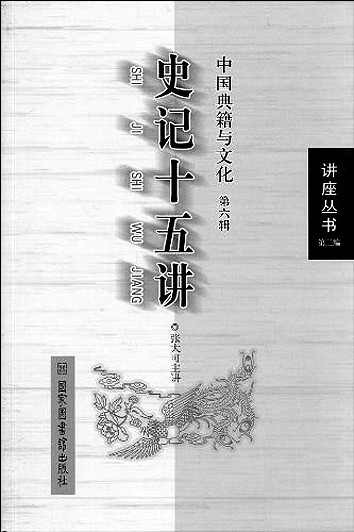
丁波供图

丁波供图

丁波供图

张大可(中)与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丁德科(右)、秘书长丁波研究《史记疏证》编纂工作。丁波供图
张大可,1940年生于四川省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任教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研究所。现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兼任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著有《史记研究》《史记新注》《史记文献学》《史记论赞辑释》《史记十五讲》《史记史话》《司马迁评传》等。
司马迁写《史记》,自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又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由此可见,想成为司马迁的知音着实不易。但张大可偏偏是一个迎难而上的人。
考入北大
张大可自幼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张大可1940年12月出生在四川省长寿县(现重庆市长寿区),婴儿时,坠地伤了头盖骨,险些丧命。他6岁入私塾识字,后随父读书。10岁时,父亲去世,家里生活困难,无力供他上新式学校。当地云集小学的校长徐国钧是张大可读私塾时的老师,很赏识张大可,专门找到张大可的母亲,动员张大可入学。母亲狠下心,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长子读书。
背负着一家人期望的张大可,越过初小,直接读了高小。从他家里到云集小学有近8公里的路程,中间还要翻一座山丘,爬二百余级台阶,单程就要走两个小时。每天清晨,他喝两碗菜粥就去上学,中午饿肚子,等到放学再爬坡翻山回到家里,备尝艰辛。作为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张大可每天下午回家吃完饭,还要到村外挑水。等水挑满了,天也就快黑了。家里买不起油灯,他只能借着傍晚落日的余晖抓紧读书。两年小学,张大可就是这样读下来的。
又经过两年边劳动边自学的时光,张大可终于在1954年考上长寿一中,后又进入江北一中读高中。在江北一中,虽然有助学金,但张大可的生活费仍然有缺口。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时而给学校食堂担煤炭,时而帮镇上工厂送硫酸罐,仍然是边劳动边学习。
1960年的暑假,张大可在镇上赶集,偶然邂逅了一位大学生,胸前别着省内一所大学的校徽,张大可主动上去搭讪,想了解下那所大学的情况,可是对方很冷漠,张大可不服输的劲儿瞬间爆发,心里想“有什么了不起?等着,明年我别一枚北京大学的校徽给你看。”1961年,张大可参加高考,凭着周密的规划和还算不错的底子,如愿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硬读”《史记》
张大可入学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来到北京大学,与古典文献专业新生座谈,还带来了新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史记》是古典文献专业的必读书,张大可果断购买了一套。
《史记》首篇是《五帝本纪》,张大可初读,感到佶屈聱牙,对内容却不甚了了,反复重读,还是不得要领,不得不将其置之一边。过了一阵,他又心痒难耐,重新拿来阅读。这次跳过《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直接读《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终于有了一些阅读的快感。从此以后,张大可专门挑《史记》中故事性强的列传去读,今天翻这一册,明天翻那一册,跳来跳去读,先易后难,读不懂的先放一边,逐渐就进入了《史记》的世界。随着理解的深入,张大可又改变了阅读方法,不再按本纪、世家、列传的顺序读,而是按时间和相关史事人物分组阅读,如春秋时期,按春秋五霸集中五组相关篇目来读,战国四公子列传为一组来读,重要史事如长平之战、秦灭六国、楚汉相争,集中相关篇目,带着问题读。若干篇目反复读几次,兴趣日益浓厚。
张大可仔细计算了自己的时间,零散的课余时间加上星期日,再加上寒暑假,一年365天有240天可以用来读《史记》。《史记》130篇,两天读一篇,他一年就能精读一遍。心里有了底,张大可规划了一年半到两年通读《史记》的计划,每周用三分之二的课余时间精读《史记》一篇到两篇,三分之一的时间读相关参考书。计划制定了,张大可天天抱着《史记》读,同学们善意取笑他是“司马大可”。
为了读懂《史记》,在反复阅读《史记》原文的同时,张大可还找来了崔适《史记探源》、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郑鹤声《司马迁年谱》、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著作,以及报刊上的一些相关文章,了解了一些《史记》研究中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虽然此时的张大可还未完全读懂《史记》,但对前辈学者关于《史记》研究的一些成果也有了自己的认识,同时下定决心,要集中一段时间对《史记》断限、亡书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
从1962年年初到1963年夏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史记》130篇,张大可通读了其中的115篇,只剩下《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和“十表”未读。虽然其中一些精彩的纪传,读了不止一遍,但张大可不甘心只是把《史记》当成小说去读。他要用史学的眼光分析《史记》,那“十表”就是绕不过的硬骨头。
1963年暑假,张大可没有离开北大校园一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集中时间全力以赴投入“《史记》攻坚战”。首先,他利用两周时间,解析《史记》十表。
张大可发现,要读懂《史记》的表,首先要拆解表,于是他用最笨的办法破解十表的结构。以《六国年表》为例,周、秦、魏、韩、赵、楚、燕、齐从左到右分八行,从下到上依年代分列,会盟征伐,兴衰成败,大事尽列其中。张大可把《六国年表》的内容从表格中打开,一条一条排比,改表为长卷叙事,把表中的内容展开成一条一条的资料。各国的王位继承、相互征伐,如果用叙述的方法记事,既不连贯,还会有许多遗漏,不成体系,而用表,就可以把同一时段各国纷繁的会盟征伐、兴衰成败有条不紊地展现在同一平面的一页纸上,一目了然。改竖排列表为横排列表,十表的本质清晰呈现:一个用表格展现的历史发展时空坐标。用了两周时间,张大可按此法改造了《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他发现,《史记》十表蝉联相接,展开的是三千年的时空坐标,提纲挈领,摘取历史大事,划分历史阶段,展现天下大势,是《史记》的骨架和大纲。二十年后,张大可借鉴司马迁作表方法研究《史记》,每写一篇专题论文,必先作表,然后行文,写作效率大大提升。有的“表”直接融入了论文中,他的成名作《史记研究》一书中集中保留了二十余篇“表”,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研究《史记》,张大可下的第二个“笨功夫”是统计《史记》字数,这是研究《史记》流传过程中续补、窜附问题的基础。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太史公书”“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后世流传的《史记》各种版本字数与司马迁自报字数多有出入。张大可统计的是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的字数。当时没有电子文本,他只能用手工,以三个字为一组,数到一百就是三百字,用铅笔在点校本旁边标记“1”,再数一百,标记“2”,依此类推,数完一篇将总字数记于篇末。用了两周,张大可最终统计出标点本《史记》是555660个字。综合崔适、余嘉锡等学者对《史记》亡篇及续补、窜附的研究,张大可对统计出来的字数进行了分析,对《史记》亡书及续补、窜附有了自己的思考。虽然当时还无力写作学术论文,但他把思考的疑点都记录了下来。
1963年暑假,在解析《史记》十表、统计《史记》字数之外,张大可还尝试撰写了一篇论文《也谈司马迁的生年》。张大可回忆,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支持郭沫若在1955年发起的“司马迁生年论战”。他当时并未料到,自己会深度参与后面几次论战,并成为论战中的主角。
司马迁的生年,司马贞《史记索隐》主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张守节《史记正义》主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张守节与司马贞同是唐玄宗时人,两人的记载存在十年之差。近代以来,王国维撰文力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1955年10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对王国维的“公元前145年说”进行反驳,力主“公元前135年说”。怀着强烈的研究欲,张大可认真阅读了王国维和郭沫若的文章。对他这个大三学生来说,王国维的文章艰深难懂,而郭沫若的文章则相对易读,他不自觉成为郭沫若的拥趸,照葫芦画瓢,撰写了一篇考证文章《也谈司马迁生年》,声援郭沫若。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的底稿后来遗失了,更谈不上发表了。20世纪80年代,张大可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再次参与司马迁生年的研讨,改从王国维的“公元前145年说”。张大可曾感慨,幸亏早年的文章遗失未发表,若公开发表了,他将不得不学梁启超,以今日之张大可反对昨日之张大可。
研究《史记》
1968年大学毕业时,张大可感到前路迷茫,把大学时期购置的所有书籍都当作废纸卖掉了,只留了一部《史记》,一直带在身边,时时阅读。他先是被分配到甘肃省文化局,几经周折,1973年被调到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张大可倍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教学科研同步快跑。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张大可迎来了他的春天。那时,张大可已近不惑之年,虽熟读《史记》,却无一篇科研成果,这成为评定职称时的短板。他不服输的劲儿又上来了,决心搞一场“攻坚战”,发表几篇重量级的论文。他从自己最熟悉的《史记》入手,以秦汉时期历史人物评价为突破口,制定了一个写作提纲,白天到图书馆翻阅资料,写札记,晚上在家翻《史记》《汉书》,做卡片。动手写论文时,张大可先提出若干问题,然后给出答案,一题一个条目,他戏称之为“零件”。积累了约十万字的条目后,他开始动手将这些“零件”组装成机器。方法得当,自然事半功倍,张大可的处女作《论文景之治》发表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三个月后,《试论昭宣中兴》发表在《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日《史学》版。这两篇文章在学界都产生了影响,张大可一位在云南从事水电建设的远方堂兄,看到了《光明日报》的文章,过年时专门回老家向张大可表示祝贺。
1981年,张大可在兰州大学历史系率先开设了《史记》选讲课。开设新课,第一步是编写讲义,张大可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硬读”《史记》所积累的各种札记,以及对《史记》字数调查的数据,在编写讲义时派上了用场,大学时代想解决但没有能力解决的题目则成为他攻关的对象。张大可计划一边课堂讲授一边研究,在教学中完善讲义,最终形成了多篇论文和多部书稿。
从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是张大可学术生涯的黄金十年。十年中,他撰写了《史记研究》《史记论赞辑释》《史记文献研究》《史记全本新注》等一系列学术论著。这些书考论结合,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他形象地将这十年的研究工作比喻为“把多种学术作物套种在时间的耕地上”。
疏证《史记》
1985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南京召开年会,张大可与部分参会学者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提出在条件成熟时当代学者要通力合作,完成一部集大成的《史记》集注工程。199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史记》研讨会上,张大可重提《史记》集注工程,与会学者商议先组织队伍,整理资料,编纂《史记研究集成》,为《史记》集注做准备。1994年,张大可发起组织了《史记研究集成》编委会。经过近十年努力,2002年,张大可主编的《史记研究集成》(全14卷)出版,此书着重阐释《史记》的思想内涵。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张大可任常务副会长,《史记》集注工程被确定为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集体攻关项目,正式确定书名为《史记疏证》。经过几年准备,2006年,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上,张大可提交了《五帝本纪疏证》样稿,与项目参与者详细讨论了凡例等工作细则,确定了项目的工作方针:“融汇古今研究成果于一编,凝聚当今时贤于一堂。”《史记疏证》分为题评、分段疏解《史记》原文及三家注、集注、白话翻译、集评、附录等内容,力求将两千多年来《史记》整理、研究成果汇集于一书。
2006年,完成《五帝本纪疏证》样稿时,张大可已经66岁了,他承担了《史记》百三十篇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篇目的写作任务,作为主编还承担着全书的审稿工作。全书规划近2000万字,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虽然有中国史记研究会秘书处的配合,但秘书处成员都是高校教授,科研任务重,分身无术,可以给他提供的援助也不多。有的项目参与者劝张大可放弃,靠他这个“光杆司令”无法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张大可年老志未灭,他给大家鼓气说,《史记疏证》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追求,我数十年思之念之,从未想过放弃。项目团队中我年龄最大,身体尚可,我自信可以工作到85岁,正好是2025年——司马迁2170周年诞辰,算起来还有20年,我每日拿出12个小时,全年不休,我们一定能完成《史记疏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记》研究者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张大可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也是一个善于规划的人。《史记疏证》是一个集体项目,项目组成员工作进度不一,张大可居中协调,自己写稿、催稿、审稿、改稿,和出版社编辑沟通,解决编辑提出的问题,有条不紊。因不通电脑,张大可全凭手写。因长期握笔进行高强度写作,他右手食指严重变形,异于常人,见之者无不唏嘘。张大可的老伴马瑞端喜欢旅游,她希望张大可知老服老,趁着身体还好,能与她一起周游海内外,但张大可忙于《史记疏证》,屡屡推却。十多年里,日复一日,张大可重复着在老伴看来单调乏味的学术苦行僧工作,乐此不疲。2023年,《史记疏证》终于定稿,交付出版社,马瑞端终于看到了希望,笑问张大可:“老张,你是否可以歇歇了?”张大可笑答:“快了,到2025年司马迁2170周年诞辰,我卸任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我就彻底休息。”
转战“六大史学名著”
张大可肯定无法履行对老伴的承诺。《史记疏证》只是他规划的“六大史学名著”工程中的一种,他心心念念的“六大史学名著”工程没有完成,他如何能停下来呢?
“六大史学名著”是指《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这六部典籍。20世纪20年代,曾有学者给历史系本科生开列了《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这六部书作为必读书目。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高校历史系教学参考书《中国史学名著选》,也是这六部史籍的选本。张大可认为,这六部史籍可以称之为“六大史学名著”。在他看来,只有既记述历史事实又阐释历史过程的典籍,才是史学著作,仅记载历史事实的典籍实质上是文献典籍或资料汇编。刘知几在《史通》中主张历史要做到纯客观实录,不能有作者的思考,批评《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为画蛇添足。而在张大可看来,正是因为有“太史公曰”,《史记》才称得上是史学著作。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是“成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对历史的思考。孔子作《春秋》,以一字褒贬使乱臣贼子惧,这就是孔子的“一家之言”。左丘明以史实解释《春秋》,《左传》是中国史学的萌芽。《左传》中的“君子曰”,启迪司马迁创作“太史公曰”。《史记》效《春秋》,不仅创立“太史公曰”,还“寓论断于序事之中”。《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资治通鉴》均效仿《史记》,这四部书均有各自的“一家之言”,作者的史论贯穿全书。因此,《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这六部书称得上是史学名著。
“六大史学名著”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经典,如何让经典“好读”?张大可希望通过“六大史学名著”工程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这个工程定义为“全新样式古籍整理”。就体例而言,这个工程包括六个方面:1.导读,全面评介典籍全书内容、创作主旨及价值、作者事迹等内容;2.篇前“题解”或“大事提要”。解读一篇之要旨或提示一卷之大事梗概;3.简注,即用白话文注说文本字、词、句的字面意义;4.语译,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5.段意,置于篇中划分的结构段的注文之后,提示要点;6.点评,置于篇后,或点评历史人物,或介绍历史大事,或进行文学鉴赏。就样式而言,针对不同层次的读者,这个工程设计了四种样式:1.白话本。逐句“语译”,是新式古籍整理最基本的普及样式;2.文白对照本。在白话本上加入原典文本对照;3.新注本。有注无译的整理本;4.注译本。合新注本与白话本为一体。上述四种样式的解读,均包含“导读”“题解”“段意”“点评”等内容,在张大可看来,这就是“全新样式古籍整理”的亮点与特点。
张大可是个实干家,他的“全新样式古籍整理”是在《史记疏证》工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史记疏证》有序推进的过程中,他就有计划地推出了四种《史记》整理本(《史记》白话本、《史记》文白对照本、《史记新注》、《史记全注全译》)和四种《资治通鉴》整理本(《资治通鉴》白话本、《资治通鉴》文白对照本、《资治通鉴新注》、《资治通鉴全注全译》)。张大可除独立完成《史记》《资治通鉴》整理之外,还作为“六大史学名著”丛书的主编,统筹《左传》《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名著的整理工作,如此繁重的工作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来说都是苦差事,年过八旬的张大可却甘之如饴。近年来,除了必要的学术活动,他足不出户,全身心投入六大史学名著的整理工作中。
大学时代“硬读”《史记》的经历,磨炼了张大可的意志,也让他清楚地知道,阅读史学名著有门槛,历史专业的大学生都不易读得懂,普通读者更是望而生畏。如何让史学名著“好读”,让年轻人能读得懂史学名著、爱上史学名著?这是张大可一直思考、努力实践的课题。司马迁将《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等待后世知音与他产生共鸣,而张大可不仅自己要做司马迁的知音,还要让更多的人读得懂司马迁、读得懂六大史学名著。在张大可看来,这是他们这辈学人必须完成的学术使命。
(作者:丁波,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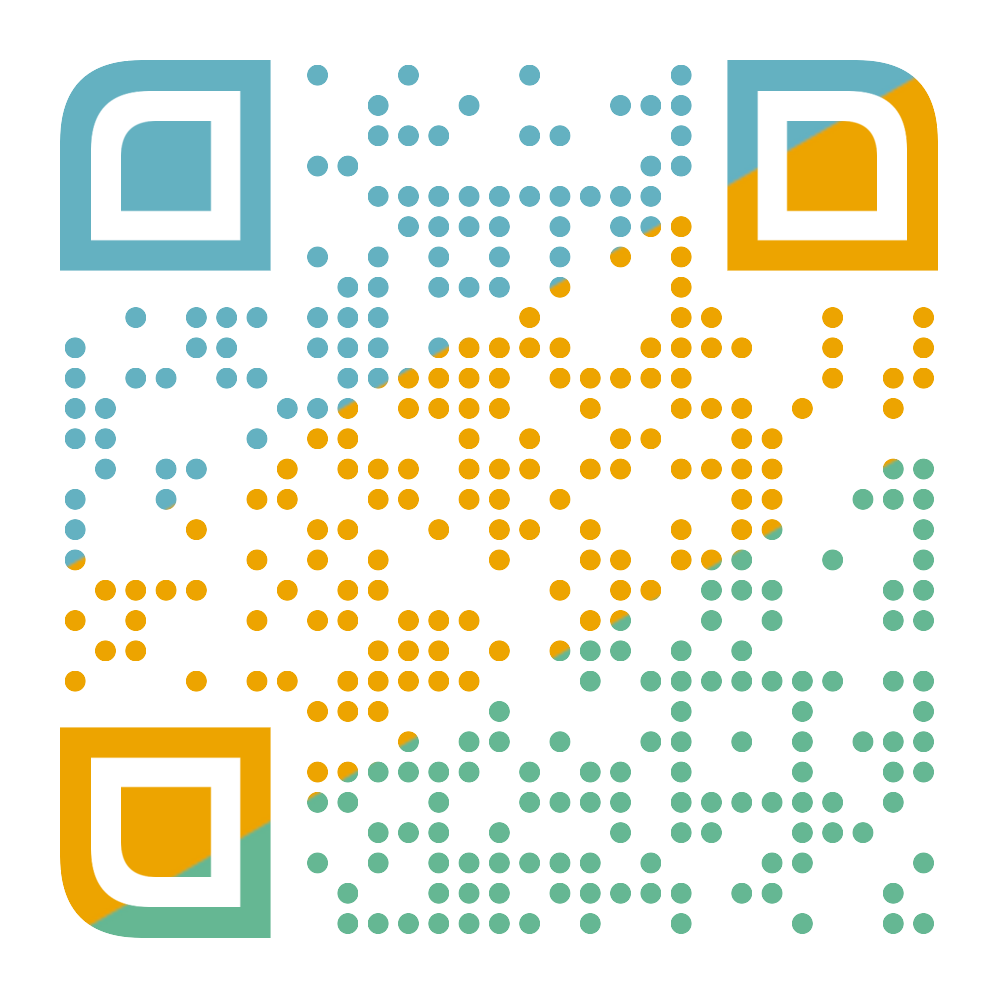



用户登录
还没有账号?
立即注册